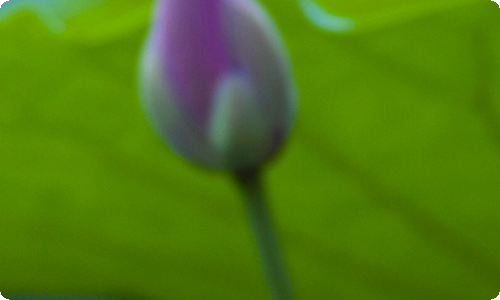
正午的艳阳直射在朱红的墙砖上,我站在门口温热的砖堆上,左手捏着一块板砖,脚下的砖块上有几点缩小中的汗渍。表弟就站在我身边不远处,刚把一块红砖放下,手还按在砖块上,突然压低了身子。
“快!全员隐蔽,二叔……啊不对,鬼子到了!”他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握起身边的一把玩具手枪。我和其他人都放下了手里握着的砖,慌慌张张地跟着他蹲下。
我们现在在清平村的一片砖堆上。砖是二叔盖房时剩下的废砖,没人要,也没人管。这里就成了我们玩打仗游戏的“基地”。砖堆最里面的一圈砖被我们掏空了,变成了带射击孔的掩体与坐着磕屁股的板凳。
“哥,你那边的,你,这边。”表弟装出副团长的派头,用玩具手枪指着左侧的枪孔,另一只手指向右侧的枪孔。
二叔正慢慢的走着。右腿刚刚抬起时,眉心,心口,左手各挨了一发橡胶子弹。
“喂,小崽子们,注意点安全。”二叔放下了腿,转向我们这边,脚边落着三粒圆圆的橡胶块,眉心处有一个小小的凹陷,表弟直起腿,胸膛高出半截掩体。
“喂,二叔,您应该已经死了,我刚刚爆头了呀!”“行,行,二叔走到那边了再算我死吧,哈哈哈”。二叔脸角上扬,喉头一动一动,发出有点嘶哑的笑声。
二叔走远了,我们全都站起来,顺手又抄起半截砖头,放在掩体上。我们长高着,掩体也长高着,阳光倾斜着,挥洒在我们身上,我看着表弟的脸颊,几粒汗珠划落着,反射出一片金光。头发也沾着水,头顶似乎升起了水气。
“喂,你什么时候搬去新家”。我紧紧地眨了下眼,缓解鼻头涌现的一点酸楚,汗水申掺了一丝泪珠。
“别一副我要死的样,不就去焦作么,又不是不回来。”表弟没有回答我的提问,眼角处似乎多了几点汗珠。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清平村的经历,这也是我与清平村无言的诀别。
第二年,家中的樱桃熟的时候,一树的绿叶随风摇曳,红通通的樱桃随着随着枝条摇晃,骄傲地向着世人昭示他们的成熟。这一年,我和表弟都上了初中,课业的大山压制了我们的幼稚,逼迫着我们成熟。
手机闪烁着,通话的按钮变成了红色,电话通了。
“今年去清平村么?”
“不了,作业太多……”
也许,我们告别彼此,告别村庄的同时,我们也与我们欢快无忧的童年一同作了诀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