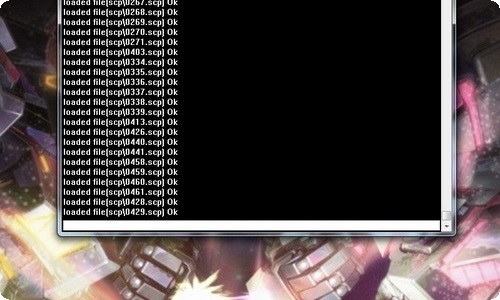
每年的清明似乎总是要下点小雨,我曾好奇地仰脸问她为什么,她靠在桌边,额前银白色的碎发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谁知道呢?”她浅笑着,手上一刻不停地包着饺子。
多么奇怪,上天竟也知道这一天的不寻常,要施法布雨营造氛围。
什么时候学会包饺子的我已不记得了,但毫无疑问是跟她学的。
小孩子天性闹腾,包饺子也不肯安分的,挑馅的勺子甩得飞起,满手沾着面粉乱拍,满桌狼藉自然是我一人的功劳。她佯装生气,不轻不重地拍打一下我的手背,再不轻不重地呵斥两声,我便略有收敛,安安静静包两只饺子。不经意间瞟一眼窗外,哟,才四月就有蝴蝶了?索性把包了一半的饺子往桌上一丢,就着满手面粉要去扑蝴蝶,她朝我飞奔而去的背影笑叹一声:“你呀……”
满锅的饺子热腾腾地冒着气,不浓不淡的香味引得人食欲大发。他们在整理袋装纸银,在追忆曾祖父曾祖母的过往,可我对他们实在是半分印象也没有,自然也谈不上伤不伤感。我拿着勺在锅里翻找半天,想找找哪两只饺子是我包的,她便急急地赶过来——自然是担心那一只只晶莹的饺子被我搅破了皮。她佯装仔细地在锅里搅动一阵,拣出两只来,将碗推给我:“呐,你包的。”我也不追究真假,她说是那便是了。
那天的饺子是什么味道早已记不清了,但那滚烫的碗,升腾的热气,至今记忆犹新,恍若触手可及。
我的口味一年比一年挑剔,她做的饺子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令我满意。或是皮太厚,或是馅太油,她却从不介意我的挑三拣四,一次次的做出改变来迎合我的口味,她为此跑遍了附近所有能买到饺子皮的面皮店,甚至尝试过在馅里加两勺白糖提鲜——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一碗温热的饺子,冒着热气,她坐在对面,面孔有些模糊,依稀可见期盼。眼睛突然被热气熏得有些发酸。
汪曾祺老先生曾在沽源采到一朵大蘑菇,精心晾干,年节回京时背至家中,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她也曾清晨五点就踏上三轮车,要去菜场挑最新鲜的茭白,最好的精瘦肉,那时天还只是蒙蒙亮,只是为了一碗温热的饺子。
桌上一碗饺子,热气袅袅一如往昔,她似乎也还坐在对面,是触手可及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