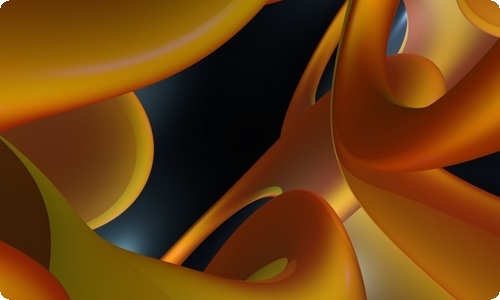
暑假的时候,回了趟老家。
记得小时候,家就住在农村,实实在在的农村,用的是那种土灶,小时候的我还帮外婆吹火,吹不到,就拿一块硬纸板在旁边使劲的扇,最后还是把自己呛了。央求舅舅把自己抱到楼上,那时没有扶手,舅舅抱着我,脚底下的木板楼梯吱嘎吱嘎的响。外婆仍然在灶前忙活,那火光,至今还在我脑海里跳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住了,偶尔老鼠从地上窜过,吱吱乱叫。
小的时候父母白天都上班,我就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外公把我放在平板三轮车的后面,自己坐在前面,穿过大街小巷,口中哼着遥远的歌谣。小的时候嘴拙,不会讲方言,普通话倒是说的流流利利的,外公一句一句的教,可是至今仍不会说。因为家里讲的方言有两种,从小就是混着说,等于根本不会说。于是出门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就不好回答了。户口已经迁走了,说是本地人吧,本地话不会说,说你是其他地方的人吧,讲方言的时候偏偏有本地腔,每次都要解释很久。
爸爸的地域性很性强,每年都要带我回老家,姐姐带我去以前爷爷的老房子,据说我出生到一岁都住在那里,刚走进去,就有一只老公鸡围过来,警惕地盯着我,做出要掐架的姿势,当初,我也是这个房子的小主人,这里曾经是我的家,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别人”的家,公鸡始终守护着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已经远离人世了,而他的子女,也各奔东西。
惨白的蜘蛛丝挂在墙角,门口的橘子树也挂着青绿的橘子,可是就算熟了,也再也没有人来采摘了,残破的桌子还摆在门口,门微微敞开着,像是在等待有一双手推开它,门槛已被虫蛀出了洞。
在那个面朝黄土的年代,没有人告诉我爷爷,他会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还是农民,一个嫁给了小老板,最小的那个当了体育老师。也没有人告诉我外公,他会有三个女孩两个男孩,其中一个语文老师嫁给了体育老师,生了个斜视的女儿。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年就这样过去了,在对未知的憧憬和迷茫中让时间顺时针旋转,直到沙漏最后一粒沙的落下,或华丽或无闻的落幕,留下一个仍然在继续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