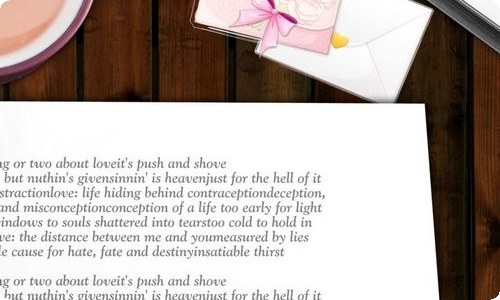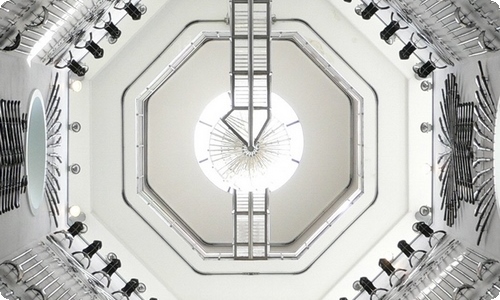冬日的馄饨,香!
寒风刺骨,天好冷。
裹紧羽绒衣,拎着一袋馄饨皮儿,哆嗦地站在红绿灯前,哈着手,以便获得暂时的温暖。树,如秃顶的中年男人,屹立在风中。临近春节,街上人烟稀少,仅有汽车在寒风中奔驰。但挨家挨户的门窗倒是灯火通明。许是都回家团聚了吧。我瞟了眼手表,抬头注视,仍在三十徘徊的数字。不自觉地笑了笑,仰望无尽的夜空。
迈步走在空荡荡的街道,受着风的袭来。发觉回家的路越发悠长,自在、无拘无束却又伴着孤寂。
暮色中,我加快脚步。风席卷着头发,丝丝缕缕,贴在眼角。我只得用另一只手,那只没提袋子的手,轻轻拨去留在眼前的杂碎。
乘着风,再次加快步子。墨色越发浓了,着实令人惶恐,我想逃离。
越过几盏红绿灯,才终是在夜色中望见熟悉的地方。抬头便可瞅见那建筑物第5层的那抹赤橙。那是为我亮起的灯,我莫名地心安。
穿行在楼梯间,直达目标。我敞开大门。前脚刚入,随之传来的是母亲加了个“吗”的肯定句:“回来了吗?”“嗯”我应了声。她盘着头发,手拿菜刀,系着还是满满少女心的围裙就朝我走来。我打量了她一身,笑道:“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跟小姑娘一样。”她低头瞧了瞧,嘴角含笑,似是回忆起了什么:“呵,哪有。这是你四年级绘画时买的,你嫌它丑,我便穿了。”
闻言,我沉默了。张口却不知说什么,只得一味地用傻乐来掩饰心中的苦涩。
厨房里,母亲在刀板上切着猪肉。忽地回头问道:“欸,馄饨皮儿买了吗?”
“嗯”。
“是丰源菜场边那家吗?”
“是。去那买的人还挺多。”我应声答着。
母亲面露微笑,唤我坐下。赤橙的光晕笼罩,在寒风中倒别有一番风味。
母亲似打开了话匣,拉着我散讲。她说在她的童年里最爱便是馄饨。那种美味是别的美食不能比的。小时,为了在冬日里尝上一口,不知要同祖母撒娇多久。
我静静盘腿坐着,当一位聆听着。我清晰地看到母亲面上的笑意,和她直通眼底的快乐。那就是幸福吧,我琢磨着。
她接着倾诉,同我传授做馄饨的秘诀。
“猪肉要好,肥瘦相搭,剁成细小肉末。肉里还需要放盐、姜丝,少许料酒、香油好入味儿。”
那时我还懵懂,只是不断地点头。母亲倒也不在意,只是一个劲地,自顾自地背着菜谱。她说,曾几何时,祖母也这样同她诉说。那时年少,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倒也是种怀念吧。
母亲边说,可手上地活儿却没停。端着满满一盘馄饨朝厨房走去。开火,倒水,她将饺馄饨一个一个,慢慢投放入锅中。听说是为了不让馄饨粘在一块儿,可我倒觉得是想聆听馄饨入锅时的歌声。馄饨一个一个泡舒服了便接踵浮出水面。母亲从冰箱里拿出准备好的地虾干、榨菜。捞出一把,撒到沸腾的锅中。
我好生佩服,母亲竟将简单的步骤做得如此细致,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馄饨好了,端了出来,热气直往上冲。香味弥漫着寒风中,我深吸一口,香味灌进鼻间。我拿出勺子,捞了一个,放在嘴种含住,轻轻咬破,肉味儿冲破阻碍直窜胃里。
寒日里的馄饨热腾腾、暖乎乎。全身被热气包裹,自然是舒适极了。
又逢一年冬季,我来杭州拜见祖母。
祖母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将我拥入怀里。
“宝儿,知道你爱吃馄饨,楼下新开了家,带你去。”我满怀高兴应下了。
寒风吹啸,夹带着雪。杭州的冬季是能见雪的,白花花的,覆盖城市,美极了。我们迫不及待地跨入门店,那人声鼎沸,形形色色的人们寒暄着一年来的苦楚。我们在角落里落了坐,点了一碗馄饨。看着面前泛着热气的馄饨,异常温暖。可尝了一口,不禁皱了眉。馄饨的馅多,皮厚,同饺子无多大差别。愣是不信,再尝一小口,仍觉得不自在。这味儿,怪怪的,不是熟悉的了。
可周围的人们倒吃的自在,欢天喜地。
或许只有离开故乡,远在他方的浪子,才会知晓那属于家,充满温暖和爱的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