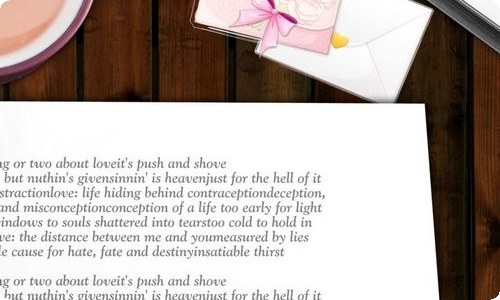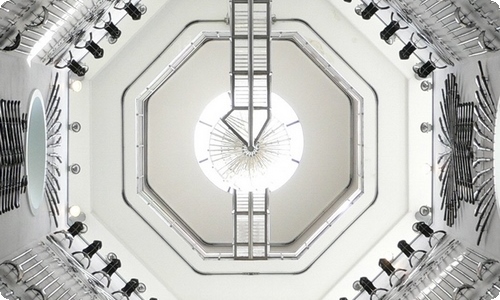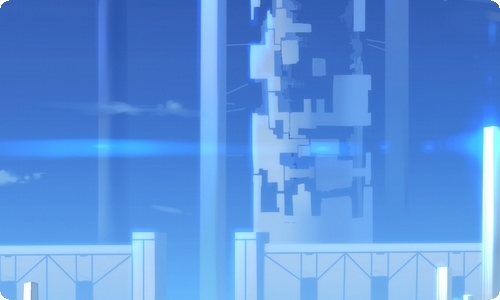
老家村前曾经有棵粗壮挺拔的洋槐树。据老人回忆,这棵树年轻时是巨大的树冠华荫如盖,素淡的花苞满树开放,满院流溢着醉人的清香。
如今的它饱经沧桑,已经很老很老了。它完全是个老人的模样,凄凄凉凉,远处望来那堵单薄的墙似乎承受不了的那厚重的身躯,那饱经沧桑的躯干啊,树上的裂纹是那样的多,每当下雨时,雨水顺着裂纹流下来时走的路,似乎就和大槐树这一生走的路一样多。每当有人们在夕阳临傍晚的时候出来,不禁要微微叹息一声似乎在念叨着:“老槐树啊,你也老了,还是不禁时间的冲刷啊。”
初春的槐树下也尽是故事。一位残疾老人,一位失了双腿的老人。每天用双手划着滑板,背着修鞋箱在榕树下吆喝着:“修鞋喽!修鞋喽!”但是理会他的人很少,生意一直惨淡。哪一天运气好,有人找他补鞋,他便受宠若惊地连忙接过:“好嘞,好嘞,保证一会儿就给你补好好。一定像新的一样。” 他的行当简单至极,一架很小的织补机、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零碎物件:橡胶皮、小钉子、小铁锤、锉刀、剪刀、搭扣、胶水、线头……他埋头于他的活计,鞋跟在他手上翻转,一双手——怎样的一双手啊,枯树枝一般灰黯的色泽,粗糙厚重,布满了裂纹又像那些因干燥而龟裂的土地,在用强力胶水粘合的时候,他直接用手摁上去,丝毫没有将皮肉黏在一起,由此可见这一双手早已背负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再也没有什么足以洞穿其间,窥见它本来的面目。指甲极短,然而每一只指甲盖的四周以及指缝间塞满了污浊的黑色——那也许是永远无法用清水洗净的黑色,深深地植入皮肉,渗入岁月的深处。修好鞋的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把鞋交出去,对付钱的主顾:“谢谢谢谢。”
一天过去了,收工回家。修鞋老人叮叮当当地收拾着家当,划着滑板,艰难地向前滑去。只剩下我独自思绪。抬头仔细一看,满是裂纹的槐树,竟在一处枝头,冒出了点点嫩芽。
我的心,被那不起眼的一抹绿,重重得撞击了一下。
枯树有新芽,它受过如此多的磨难,仍旧选择逆流而上。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正如这修鞋老人,永不言弃,勇往直前,只进不退,迎来生命的曙光。
这是一场奇妙的遇见,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