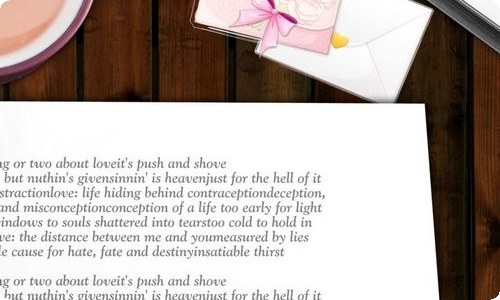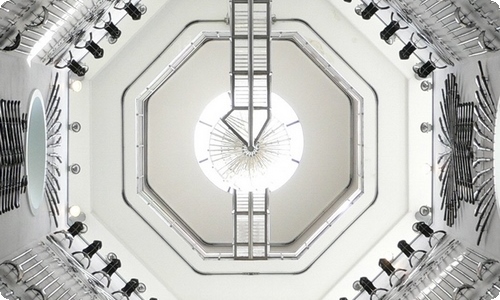后来我才明白,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东北父母,无论多么爱,我也不会说一句我爱你。因为他们早就已经把深切的爱意播撒进生活的土壤里,并甘愿用一生的辛劳去耕耘。——题记
冬日,午后的阳光虽明亮,但伸出手轻轻触碰,却还是感到一丝入骨的寒意。我与父亲走在林间的小路,他握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慢慢走,他的手温暖、宽厚、有力,恍惚间,我想起了那年冬天,故乡下的一场大雪。
雪后的空气,清新冷冽;雪后的暮色,昏暗中有了一丝朦胧的意境。父亲急匆匆穿了件黑色的大衣,就要去接几里外学校放学的母亲。四岁的我趴在门檐上,糯糯地叫了句:“爸爸,我也想去。”
我踏着小碎步在父亲身后跑,父亲在前面大踏步地走着。苍茫的暮色里,映衬着一大一小两抹身影。父亲回过头,问我冷不冷,我摸了摸冻红的鼻头,仰着头回了句:“不冷。”他敞开毛呢大衣,我一溜烟钻了进去,父亲的大衣里好暖,小小的我头只能到父亲的腰间,大衣里一片漆黑,但是爸爸在,我一点儿也不怕。雪地里,一大一小的脚印在上面嘎吱吱地走着,给这寂寥的冬夜,平添了一份温暖。
想到这儿,我咧开嘴角笑了。但是蓦地,我的眼眶又有些湿润,抬眼看去,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在了我前面,而他身边是我的母亲,他们互相说笑着并肩走着,本应该温馨的画面在我心中却有一丝心疼——我看见昏黄的暮色映在他们的根根白发上;我想起了青春期以来,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打击和伤害;我也想起了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为我所付出的一切的泪水与汗水。我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妈妈。”他们转过头来,我看见他们微笑着,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好似老树回春。我跑上前去,牵起他们的手,一同向前走去。
恍惚之间,他们都还是我的天空,我的大树,是我永远依恋的家。可是一转眼,他们就老了。岁月的积雪堆满了发间,作家朱天文说:“父母的白发不是老。”看到这儿,我的眼泪落了下来。其实,亲情就是雪中的炭,锦上的花,不是吗?因为我都来不及慢慢等待,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爱他们吧。给爱一个支点,因为两代人生命的衔接处,光阴只是窄窄的台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