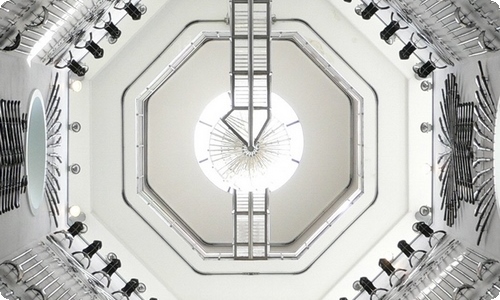那棵槐树来自昔年,却留在昔年
这昔年,是六七年前我在蔡家坡度过的。蔡家坡的西北机械厂里。
在这个数不清几只胡同几道巷的厂区里,有老妪坐在楼院里聊天,玉兰把夏日滤成一片绿荫,烈日从叶隙落下一枚晶亮的光,恰恰点燃起一朵紫红的胭脂花以及--这棵槐树。
但我只是看树。
说来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何在顽皮的年纪看树呢
你看啊朋友,这棵槐树的枝木看似痛苦扭曲,芜杂纷乱,但它却在一撇一折中画出自己的生命。那嫩叶是生命的门窗,枝干涌动的生命染得一树的青绿冠。
于是,我在晚霞悠悠下看樹,在白云碧霄下看樹,在大雨磅礴时撑伞看樹。
日月星光,天地苍茫,也似全被树敛起来了。枚枚碎光漏叶罅,又在葳蕤枝条下拼一卷的明光。
接回宝鸡后,已然是常未想起这事了。几年过去了,我深知老树不会长但新绿是会绚烂起来的,笼着树呢。
再次回厂,曾经在老树旁的一列商铺原是水泥墙也都贴上了白瓷砖。树不是建筑,它有自己的活法,任周围几般变化,它根深蒂固着,清闲地敛着碎光,一片星辰。
绿叶也确实芸芸,它哪曾改变几分?清凉的绿叶一直是清凉的,叶间的光芒一直是璀璨的……
那恰恰是最后一次见它了。
再回去,就是发电机‘哐哐’的响,一片平地了。
再也没有一颗有心跳的树了。那天,夏风焦渴,水槽干涸,凄草茵茵,不见槐树芸芸。
那棵树,留在昔年,但不是它的选择。
记忆中的心跳证明了它想横亘时间长河,落叶,开花。
南天竹正冒出心绿,沿阶草更是踊跃生长,但那抹会敛光的新绿却被埋在时间的泥泞中长也长不出了。
厂子里,几条胡同几条巷我数清了,昔日擀面皮夹饼吃不上了,贴上白瓷改头换面的超市我忘却了,只有这碧影中的老槐树让我凝噎了。
“小伙子,西北机器厂怎么走呀?”
“大爷,这儿就是啊。”
“哎呦,这的变化可真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