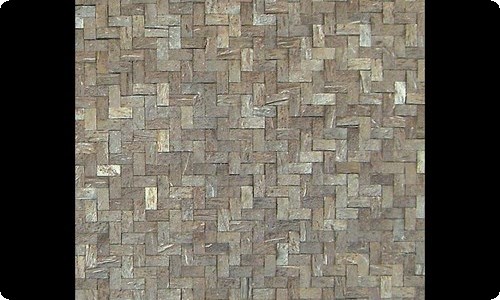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双纯真的眼睛。
我九岁那年,父母在乡下买了一套房子,邻里很多,其中最熟络的一家,养了一只金毛,主人乡下的,不会给狗起名字,就五月、五月地叫,因为它生在五月。
我经常领着它来家里玩,那时它才四五个月大,倒没什么出众之处,唯独那双眼睛纯得就像云,热烈得就像光。我常能从那双极黑的眸子射出的万物里看出斑斓之色,是绝美的成语亦无法形容的那种美好,是它自己对于世界的那种不经意而含蓄的深爱。那种不谙世事的单纯,那种不掺杂质的惊喜,是极为罕见的。我想,这该是它自己所赋予尘世特殊的定义。我带着它骑车,带着它在初冬的阳光下放风筝,望着它湿漉漉的小鼻子嗅闻着干冷的空气,泥土的气息,眼里浸满欣喜,那种彻彻底底,轰轰烈烈的欣喜。它在一片死一样沉寂而灰蒙蒙的世界里吐着舌头,欢喜地跳来跑去,追着纸雁风筝,从街的这一头,跑到那一边,又兴奋地折返。我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却也不由得注视起身边的景色来,虽不算缤纷,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有一种用最纯粹的面目示人的、别样的风姿。原来,风景是世间万物。人们一路曲折,为了诗和远方,其实,眼前却并非苟且。这样深刻的道理,竟然是从狗身上领悟到的,我哭笑不得又意料之中,毕竟,它通人性,有我所感受不到的魂魄,懂得多少人所不懂的珍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竟然从它身上看见了久而不愈的伤口,隐藏在厚重却不华丽的毛底下。它长大了,却还似小时候的瘦小,我单手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抱起来。我心疼地为它上药,梳理它凌乱的毛。它的眼睛里有了些许细微的变化,虽然依旧纯粹,就像一块冰,一块在光下泛出色彩的冰,但却多了一丝无奈和失落,不甚明显,但我还是注意到了。但这又能如何呢?我无权干涉旁人的生活,唯有一个拥抱可给,一串脚步,一道目光可送它归家罢了。它仿佛也知道我的苦衷似的,从不拽着我的衣角难以移步,也从不待到天黑,甚至连我想和它对视时,它都闭上眼,执拗地把头深深地埋进我怀里。
某一天,我同往常一样牵着它的绳子,把它系在那家人的门把手上,转过头去。身后,一阵风起,叶子如雨般落下,树上残存的叶子沙沙作响,如同一首轻轻的挽歌。树只有看着,看着那些昔日的快乐随着那一秒,成了难以拼凑也难以追溯的遗憾。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它。
听人说,它在一天离家出走了,因为主人的殴打,因为生活的凄苦。那是一个暴雨天,淫雨霏霏,连绵不绝,甚至池塘里的冰,都被打得左右晃动起来,发出颤栗的声响。五月走之前,还来过我家,只可惜我那一天出了门,错过了这仅有的一次告别。那人说:“五月真的难以辨认了,那天碰见它的时候,它那双眼睛,那么无助,又那么无奈,又复杂又凄楚,还有很深很深的愤恨,就像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家人。我想叫它回来,但它好像突然变得特别胆小,一下子就跑走了。奇怪的是,它一直在摇着尾巴。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条亲人的狗。”我默默无言。小镇的尽头是山,山的尽头是城市,城市的尽头是另一座城市。但它的尽头呢?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只有祈求,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留给这个让它又爱又恨的地方最后的背影,仍在摇着那根短短的尾巴。是劝慰?是告别?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理解为一个纯真的灵魂最后的自白。即使生不如死,也要死守着最后一丝纯粹的阵地,也要选择相信。这是它的抉择。
我一直在等它。
今年,我养了第一条自己的狗。在领走它之前,我轻轻地说:我会对你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它的眼睛也很纯粹,我仿佛从它的眼睛里看见了久违的斑斓的世界,也看见了五月。它在那年初冬的阳光下,那么快乐地追着风筝,就像一张昔年的照片,尘封成了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