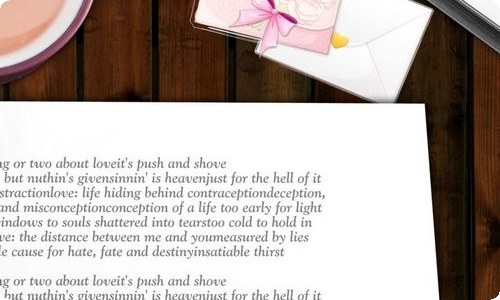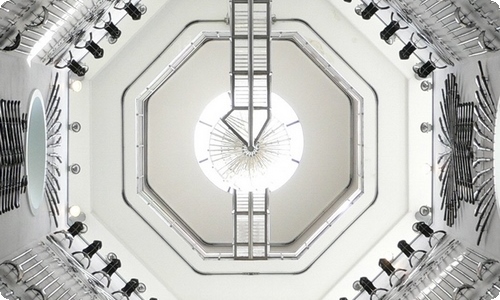篇一:卖炭老翁
汤辰杰
风伯又发威了。空气中一层层的涟漪紧挨着,拨动着,越来越快,行人都察觉到了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在澎湃。路上细小微尘都被裹挟着,夹杂着,随风呼啸而来,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它的脚步。树在狂风中不断摇摆,草俯首称臣,云避之不及,花骨断筋折。
一个老者,拉着一辆破旧的板车,坚定地向前走着。狂风对他一次次地冲击,但他岿然不动,如同一座山。
风佩服他,不敢再肆意猖獗,乖乖地退了下去。直到这时,我才看清他的面貌,已经直不起来的脊椎,沟壑满布的面庞,粗糙的大手被染成黑色。汗珠在地上流下一条水迹。他的年纪看上去已超70岁,花白的胡子布满下巴。
我忍不住跟随他走,只见他拉着车,艰难地前行着。每到一家店铺,他都挤出一点笑容,凑上去:“好质量的煤要吗?便宜价格,再加个折扣。”铺主正眼都不看他,“都这个年代了,谁还用煤呀?都用燃气了,你下次别来这儿了,看着眼烦!一边儿去,别影响我做生意!”他也不争辩,连连说:“对不起”,拉着车慢慢地走了……
到了一家店铺,铺主一下子定了一百多斤,老者似乎都忘了怎么笑了,只不停地用毛巾擦脸。他说了个65的价,铺主十分熟练地开始讨价还价,他只淡淡说了句:“本钱赔不起啊!”铺主见了,便没怎么为难他,定了60的价格,老者愉快地答应了。
他走到车旁开始搬煤,他努力地下蹲。用臂弯搂起将近20块煤,接着:“嗨!起!”了一声,双腿使劲地发力,整个人慢慢站起。他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店铺旁,将煤轻轻地放置于铺旁,接着站起来,直了直腰,说:“稍等,马上好!”又走到车旁,重复着刚刚的动作。一次次的动作,他努力着,几缕银发贴在额头上,汗珠渗了出来,搬完煤,手已经完全黑了。
一个煤炭老翁尚且如此努力,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奋发向上呢?我看着老翁远去,充满敬意。
篇二:做笔人
张爱钟
记得在老南京的毛笔市场上,有一个待人诚恳,不惧风霜的做笔人。
做笔人永远很有精神,不显富态的身体,使他看起来宛如被压紧的弹簧,精悍而有力量。额头上布满细细的皱纹,大概是他每次制笔时,都会瞪大眼睛的缘故。
第一次见到他时,便被他的两只手所吸引。常年制笔的辛苦使他的手成了两截老松木,显得结实、稳健,粗粗短短的手指像三节钢铁,所以做起笔来是有条不紊,不紧不慢,刚柔并济。他制成的笔都是由他那十根富有特色的手指所做。
做笔人从不偷工减料,记得几年前,有人告诉他:“做笔也别那么认真,马马虎虎做出来就行了,反正你人缘又好,也近古稀之年了,工作了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他却把眼睛一瞪,丢开工具:“什么意思?我老了,难道不注重名誉吗?我兢兢业业了一辈子,难道要晚节不保吗?嗯?”提出“忠告”的人目瞪口呆,只得拂袖而去,留下制笔人一人在屋中沉默。
做笔人平日不善言语,但富有善心。记得新冠期间,我去他那儿买笔,却在临走前,他塞给我几支毛笔。支支吾吾的说:“看……看你是老顾客了,这几支笔权当留念。”我从他手中接过笔,再小心地贴身放好,又用满是疑问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对上了他充满惭愧的眼睛,我肯定,这其中有问题啊。
回家一看,发现几只笔与原来几只笔相比,好像偷工减料了,但索性用起来还算顺手。第二天我满心存疑的找到他,借口买笔打算问一问原因,却看见他急忙把一个东西塞进抽屉才抬头瞟了我一眼,吱吾着:“要什么?”我答:“松墨”。
他急忙投身入屋,我趁机翻了翻文件,我明白了,那是一张为疫区捐款10万的捐款书。我不禁肃然起敬,这位老人用它尽一生的积蓄,帮助了千千万万个素未平生的人,这是他的匠心。
我听见门有异动,急忙把纸放下,从他手中恭恭敬敬接过松墨,仿佛捧着一颗鲜红的匠心……
篇三:街边的乞丐
尹海容
我很久没有在街边见到他了。他是个老人,约莫六七十岁。是个盲人,话也说不大利嗦,平时就坐在街边,面前摆个有点变形的罐子,罐子里有几枚硬币——他是个乞丐。
以前我路过街上看到他时,他靠在共享单车的车尾上,屁股下垫着块破木板,身前的罐子此时握在他的手上。他的手晃来晃去,里面的硬币撞击着罐壁,发出沉闷的声响。摇了一会儿,他把手放下,头垂了下去。又过了一会儿,他大抵是听见有人的脚步声在靠近,他就慌忙要抓起罐子,但手一抖,罐子翻了,硬币撒落出来。
他便弯一下腰,弓着身子,手指在地上摩擦着,四周擦了一遍,他又往远处摸去。硬币似乎找齐了,在他面前排成一排,他那根短短得小拇指压在硬币上。从左到右,轻轻划过去,又轻轻划过来。他把头低下,左手和右手把硬币聚成一个小丘,再把它们握在左手手心里,放进了罐子。
做完这些,他把头低下,这次比上一次更低,好像刚才做的那一切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他许久没有大幅度的动作了,只有那微微动着的头才证明他是活着的。我听别人说他好几年前就在这儿了,脑子也许不太正常,每天只在傍晚的时候去马路对面买个馒头,自己只吃一半,另一半放在一旁不去管它。我瞟向他的身边,根本没有馒头,想必那一半是被某只野狗叼了去。
我正想着,他已经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向前走,走到马路旁的电线杆,他稳住身形,接着往前走,大家都没有过马路——因为红绿灯的红灯还亮着。
但大家没有叫住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或像课文中的孔乙己,我不敢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