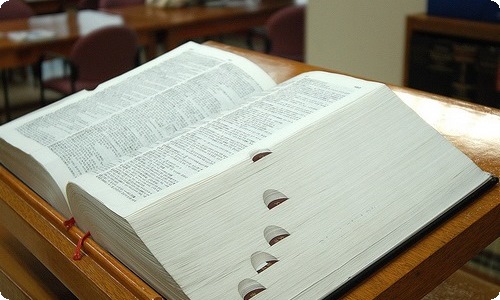
那年的雪飘落太多离愁,重重地压在心头。——题记
彭阳一四年的雪比以往几年来得更为讨喜。纷纷洒洒的,都是一大朵一大朵落在行人黝黑的睫毛上。我是极喜欢那年的雪的。这种喜欢一直持续到元旦。
那天的风很冷。太阳也特别刺眼。万物都不好看。未消融的雪结成冰爬在路面上。滑溜溜的,连母亲这种老司机也望而生畏,撂下一个“走!”就模糊了身影。我抱着花圈,学了舞蹈的腿生了根,一动不动,踌躇不前。母亲也不理我。就大步的走啊!她的脚踩在了地上,她痛不痛啊?那是她的父亲啊!
直到午间的阳光温暖了发紫的脸颊,才敢抬起了一路上都不敢抬起的眼眸,看似不经意的“瞄”了一眼不远处的红瓦房,一路被风干的眼睛又湿润了。越来越近。可爱的红瓦房传来一阵一阵的哀嚎,在只住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听着格外清晰。昔日洋溢着欢声笑语、温馨和乐的红瓦房此时却硬生生止住了我的脚步。谁会记得那儿曾是我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家啊。今我来思何故雨雪霏霏?
近乡情更怯。泪水和着悲凉的风模糊了归乡的路,打湿了路边的篙。我跌倒了,痛的眼泪簌簌地直往下掉。十三年不计回报的体贴照料;生病时衣不解带的的关怀陪伴;考砸试后恨铁不成钢的严厉斥责。一点一滴、一帧一幕,倒带般在脑海回放。
记忆果真时最毒的药。
该来的,怎么也躲不掉。故意拖慢的步伐在母亲不耐烦的催促下还是加快了起来。红瓦房,近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悲凉该是如此吧!人走茶凉、物是人非的落寞也如这般吧。擦干眼泪由着母亲穿上孝服,领到灵堂里。
从红瓦房里出来一路跑到山顶,对着那棵记忆中的老杏树才敢把压抑的悲伤发泄。没了力气就蹲在地上看着眼泪滴在雪里蔓延开来,又抓起地上的雪捏成团发了疯似的朝远处掷去。嘶声力竭地骂着老天不公,我竟不知疲乏。
三日后,我离开了红瓦房,绝口不提曾与他绘在墙上的天涯。想用最好的方式纪念,那便是:
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守护他想守护的人,就当是纪念有他的曾经。
唯此言爱,愿他于我是永生不悔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