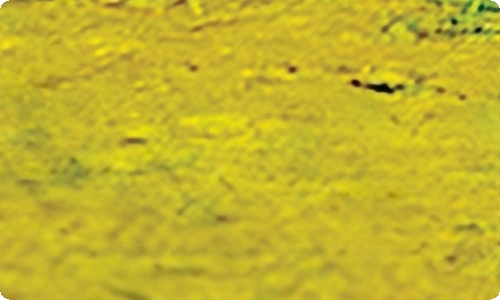
太太,一个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精彩瞬间的人。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好像真的短到一瞬间,但我却记忆犹新。
太太的个头儿不高,驼背,腿脚不利索,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而且左脚因烫伤留下的疤痕,都能把小孩子吓哭。即使身体状况不好,但她满脸皱纹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
我和太太相处的时间是在暑假,记得那时候,我带着一堆零食或端着可口的饭菜,快步爬上二楼,这时太太总会坐在阳台的太师椅上,看到我便慢悠悠从阳光处走出来,她在这时也总会说些什么,但我再也记不清,就像再也记不清她的声音一样。看着她蹒跚的步履,我总会抢先一步进入屋子摆好东西,乖乖看着太太从一沓子的光盘中精心挑选:“你不常听戏,给你选几张好听的!”我陪她看过的光盘摞起来足有一根食指高了吧。可她还总是认为我看的太少,陪她的太少。她干枯的手指在光盘中来回划过,抽出又放回,重复多次。一下午,我陪着太太看戏,太太陪着我吃零食,戏听了不少,零食也只剩包装。陪着太太常看戏曲,也耳濡目染了许多。或许是戏曲天生与我无缘,即使我能说出唱的什么,也哼不出那种曲调。太太却也只是随口一哼便十分精准。听太太哼过最多遍的曲子,我一直不曾记得叫什么名字,但也一直不曾忘记那个独特的调子,因为太太喊我名字时的尾音都带着那种独特的韵味。
太太走后我从不听戏,不是不再喜欢,也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听、和谁去听。太太走了连带着我的那份对戏曲的热情。
我总喜欢和太太一起睡。晚上,我总是会听到奇怪的声音,摸着黑从床上爬起来,轻轻靠近太太向太太询问是什么声响。但我仍记得她有一次的回答是这样说的:“是老院的那条大黑蛇。以前在老院的屋子里它总是盘在床下,陪着我,我搬家了,或许想我便跟来了。”“是真的吗?”我压低嗓音轻声的询问,好像真的怕惊着那大黑蛇一样。“是嘞!太太骗你干什么?它呀,现在应该有这么粗了吧”月光透过窗子洒进屋里,太太挥着双手讲着玄幻地故事,我听得入神了。
现在太太的房门总是紧闭,望着那扇门,望着望着,回忆便不断翻涌出来,画面定格在屋子里一老一小的身影,影子渐渐变得模糊,脸颊上躺下了两行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