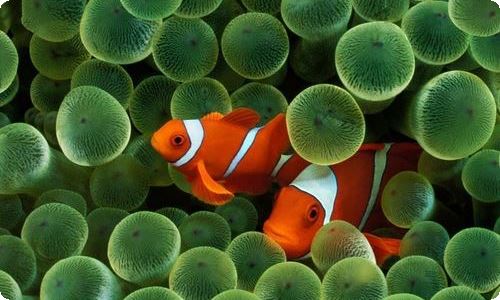
先生去世已有多年。
远处传来飒飒的秋风拂过茂林修竹的簌簌声,送来几缕桂花的清香。那半山园中微醺的雏菊,想来还在秋风中闲适地开着吧。先生的魂灵,该是融进了江边修竹的傲骨吧。
那是先生被朝廷从黄州召回京城的那年。
大概是思念那个与他御前争辩的“拗相公”了吧,先生嘱我在北上途中绕路取道金陵,他要去访王荆公。初秋的江上氤氲着两岸桂花的清香,寂静的江面上水波不兴。远远地,我看见岸边修竹深处的一个小黑点,如蜉蝣般寄于天地,见不真切。待到来人走近,才看清乃是一位苍颜白发的老者,一袭黑袍,骑着毛驴悠闲于修竹之间。先生一袭白袍,屹立在船头,捋着胡须,止不住地颔首微笑。待到上岸,先生拱手长揖,半打趣地说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荆公亦颔首,长揖而答曰:“礼岂为我二人设哉!”言罢,二人抚掌大笑,笑声回荡于天地之间,同清幽的桂香交织成和谐的旋律,此刻,天地之间,仅此二人而已。
取道江边疏竹间的小径,我牵着毛驴,随着二人一路游目骋怀,斜风夹着细雨,轻轻打在二人身上,却似浑然不觉一般。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只见先生黑发白袍,荆公则白发黑袍,二人闲游于竹林之中,似是天地间翠竹碧水里一黑一白两个清高的小点,两人相携踽踽于小径之间,不时随着徐徐秋风吟出几句诗来。谈到年轻时的意气,两人仍是倍加怀念当年朝堂之上的舍身谏诤,谈到兴起处,相与抚掌大笑。所有政见的争辩,都在此刻化成了过眼的烟云,两个年轻时的政敌,两个当世才子,两个出世之人,所有的艺术上的心灵沟通在不知不觉间弥合着横亘二人之间鸿沟。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过如此。
来到半山园,外面已然下起了江南的绵雨,荆公手植的雏菊还在雨中迷醉地起舞着。抿一口清茶,两人跽坐于几案前,修竹流水畔,落子声清脆,伴着细雨打在窗棂上的沙沙,想必这即是心灵的沟通吧。先生时而颔首轻笑,眉眼融进窗外的绵雨中,想是已然沉醉了。我不敢打搅,小心地烹上茶,让滚滚茶声与这静寂自由交织着。
明天即是告别之日。渐渐醇厚的夜色吞噬着二人的身形。两人在烛影中谈佛论道,畅论古今,笑声朗朗。
窗外的绵雨还在穿林打叶地沙沙着,黛瓦上滴下一串雨花,正落在墙角的雏菊的花苞上。微风送来幽幽桂香,江边的疏竹仍在簌簌地摇曳着,江面上水波不兴。
起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