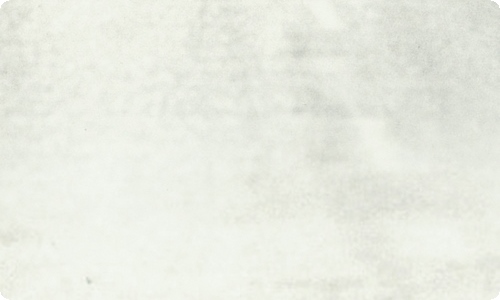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听到这首流传已久的民谣,我饶有兴趣。便问正在旁边翻看动漫书的哥哥:“嘿,你知道啥是腊八粥吗?”“八宝稀饭吧。”“那糖瓜呢?”“哈蜜瓜吧。”
屋里一阵寂静。其实,我们何止这两种东西不知呢?曾经延续千年的古代年俗,已被人们渐渐淡忘,并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消失。
变味的压岁钱
说到过年,小孩们最盼的便是压岁钱,给长辈们作个揖,道两声吉祥,就可以欢欢喜喜地拿着几百元不等的压岁钱,去买糖果、玩具、鞭炮和自己喜欢的过年礼品……仿佛没有压岁钱,这个年,就没什么乐趣似的。即使被父母“保管”着,也丝毫不影响得到压岁钱的兴致。
相传压岁钱本为压祟钱,意为压住邪祟,因为“祟”与“岁”谐音,名称才慢慢变了。长辈们在过年期间给晚辈发压岁钱,是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地度过新的一年。所以发压岁钱就成为中国年俗保存并流传至今。
“爷爷,祝您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身体健康!”我、哥哥和妹妹…正在依次给爷爷拜年,我脸上挤满了微笑,嘴像抹了蜜一样说了一大堆类似“福如东海”的祝福话语。爷爷端庄地递过红包,我恭敬地向爷爷鞠躬并迫不及待接过,一掂量,准不少!我暗喜地来到后屋,仔细一数,哇,果真是一个特大红包!不巧,妈妈这时也进屋了。我暗想,又来帮我“保管”压岁红包了。一想到压岁钱又要被没收。刚才的兴奋劲顿时全没了。
妈妈向我一伸手,我装愣卖傻:“你干嘛?”妈妈傻傻一笑:“压岁钱呢?给我保管。”我决定耍一次浑:“不给,这是爷爷给我的压祟、祝福。”妈妈见状便又使出她贯用的技俩美其名曰:未成年人用钱意识大说论:“什么数额较大,鉴于安全考虑,暂时为你保管……”我听过成百上千遍,耳已起茧,但每次都会被她那能说会道的七寸之舌糊弄得晕乎乎,感觉听着还颇有些道理。于是我又只好挥泪把红包拱手“让岀。”
不知什么时候起,压岁钱的支配权已不再属于我们孩童,却成了大人们的囊中之物。它也不是以前的“压邪祟”了。我不禁为之叹息。
守岁与抢红包
窗外火树银花,苍穹亮如白昼。花灯,照亮明朝;烟火,迎来新年。看着《春节联欢晚会》,我不由感叹:“火树银花合,星桥铁树开,年味十足啊!”
可是十足的年味也有大煞风景的地方,我准时看着春晚,妈妈也“准时”在微信上等着什么“合家欢、一家亲、愉快周末、旅游群等发红包。看着精彩的武术表演,我和爸爸不由感叹壮观,突然,“哈哈,耶斯(Yes)!五块八毛六!手气最佳!”妈妈兴奋得直呼起来。听着张杰的优美歌声,突然一声“哎呀”把我赞叹张杰的后半句都吓回去了,“两毛钱!手气真臭”妈妈嘟着嘴,懊悔得想抽她自己两耳括。
我和爸爸向她投去了不悦的目光,妈妈也知趣地捧着手机,一边大呼小叫地抢红包,一边慢悠悠地挪出客厅去了卧室。“不闻新年热闹声,但闻老妈抢红包鸣啾啾!”我和爸爸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一声。直到午夜十二点,妈妈仍沉醉于抢红包,似乎连新年的钟声她都未听到。
守岁不就是为了表达对已逝岁月的留恋之情,对新年的美好期待吗?可如今,这份留恋与期待到了何处?
鞭炮去了哪儿
年幼时候的“年”,不是从日历上翻到的,不是听大人讲来的,也不是看红纸对联、火树银花知道的,而是从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中感知到的。“叭、叭、叭叭…的鞭炮响,从冷清到热闹,从零星到密骤,从一人放鞭炮独欢到群童打炮仗同乐,这便是我幼时懵懂的过年气氛。
现在,为了倡导节约,保护环境,减少火药爆炸产生的硝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今年政府也早早地下发了城区禁放烟花爆竹的新规。难怪已是腊月二十八了都未见到以往群童们打炮仗时的身影和听到放鞭炮时的嬉戏声,小区和街道顿时冷清了不少,以前摆着五花八门、样式各异的鞭炮小摊们也不见了。我心里莫名地失落,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因为没有鞭炮放的年,终让我患得患失。大年初二,是大舅公家的年客,趁着去农村的大好时机,我便在乡镇的街头购买了足量且简单的鞭炮和烟花,在田间院坝头奢侈地感受着过年时的鞭炮乐趣,要不然今年该多无趣!
那些曾经过年前一个月就购进鞭炮销售的小摊去哪了?那些曾经一下子就把我目光抓去的鞭炮又去哪了?
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这样的景象:
一个小孩喝着腊八粥,吃着用黄米和麦芽熬成的糖瓜,放着五花八门的鞭炮,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嗑家常看《春晚》。窗外灯火摇曳,映亮黑夜。小孩,手里捏着止装着二十元美好祝福的压岁红包,甜甜地睡着了……
我希望过一个这样的传统中国年,虽然简单,但却快乐。
过年,其实不必给小伙伴们过多的压岁钱,让他们真正拥有压岁钱的喜悦,感受到“年”的气氛就好;不必熬着通宵抢着微信红包,怀念并感知就好;不必大张旗鼓铺张浪费地放着礼花,迎来新年就好。过一个简简单单、原滋原味的传统年,便是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