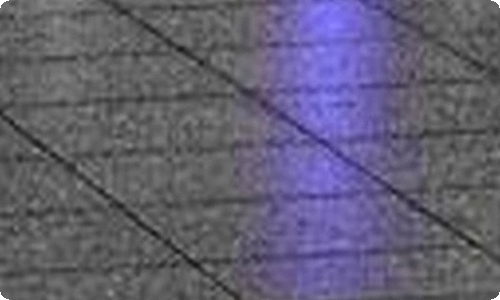我是一个怪癖的男孩。
或许还应添上些天才的色彩罢。3岁时候用海绵笔沾水,在公园地砖上大书“ABCD”之类;7岁在书法大咖们的会堂上画了几个怪模怪样的小篆“中国梦”,却莫名其妙的刊上了报纸;9岁上了全市写作“榜眼”的台位,还傻傻地咧开一排白牙。但我从不认为自己与笔有缘,只是向来引以为傲的摄影艺术——还自负地创立了个“荷花淀派”,意在以拍荷塘成名的摄影师——却从未有过丝毫的“功绩”。
我对诗词、文章尤为铭感。读到“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眼眶就湿了;轻轻哼唱《天净沙·秋思》,妈妈竟问我:“这歌是哪学的?”好……好悲凉啊!”甚至于那句“一个远游者,上车时并无背井离乡之感,光阴一逝,填充的只有挂念了”,我在床头泪汪汪哭了好久,然后便在心中抹之不去了。直到最后“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才让我呆呆愣了许久。
我胆子最大时应是3岁吧,面对幼稚的“ABCD”与大众的目光睽睽不脸红。越到后来越胆小,对蟑螂和狗愈发敬而远之。去年秋天走在路上,突然一只狗窜出来,向我疾扑,似一道白虹,我竟至于大叫一声“大哥别碰我”转身便逃。路人都笑,而我呢?看见狗仔主人脚边蹭着,惊魂未定地回了一句:“我……说的是dog,狗的,狗的英文……”
学着母亲,我十分嘴硬。10岁时,人家问我怕不怕蚊子,随即抓起一只早准备好的似蚊子丢来。我刚回答“不怕”,见了这一幕,把尾音“a”拖得抖了起来,抓起书,乱拍乱打。人家笑道:“家宝啊,你和《碧血剑》里棋盘伤人的木桑倒有七分相像。”
——我怕蚊子,而他的嘲讽,我也是懂的。
要知我虽痴,却也有生活之乐,最爱武侠小说,一边看《射雕》,一边动手动脚地演示“降龙十八掌”“一阳指”“弹指神功”,一次一个失手,一掌把一本书打出窗外,——所幸住在一楼。
我还有许多烦恼之事,只是不能细评,引用张爱玲的一句经典:
“生命是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