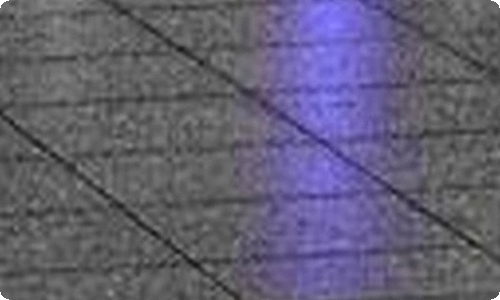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正如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本来那个人。”
——哈维尔·赛尔卡斯
人的心里住着一个“我”,你所见的,或许“非我”。我们努力将外表塑造为心目中的完美人,却忘了,那个真正的“我”。
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漂亮女人与一个衣着朴素的小伙子在公园的长椅上相遇,女子指向路边的轿车,示意自己是其主人,并大肆批判金钱与奢侈主义。小伙子默认,态度谦卑。交谈过后,女子走向不远处的餐馆——她不过是个侍从。而那小伙子却钻进车,招呼司机去了俱乐部。欧·亨利的小说为了诉说什么?那位漂亮女子的背后虚晃着我们的影子,太多人每天致力于伪装成一个完美的角色,为了博取社会地位与所谓的尊严耗费心机。于是,虚荣在人性的河底被淘取出来,久久浮于表面,人们亦无法再辨清,何为“我”,何为“非我”。
我们熟悉的,是那个施以脂粉的自己,掩盖了本心的自己。演员成了天职,尽力表演。
“非我”即不是真我,但不是所有的“非我”都完全黑暗,它的目的不是单一的“掩饰”“虚伪”,它依旧可以成为一个饱含光明的影子——当它被寄予希望和艺术。
希腊神话中写那耳喀索斯以水面为镜,见美少年,以手抚而人面消失,而后水面平静,人脸复现,狂喜,更美,欲拥抱而人面又失……直至最终趴在潭边,憔悴而死。水面的“我”,非我。那是超越了客观的艺术的我。向往美,便追求,追求非我,失真,似我非我,生于幻象。
那耳喀索斯的逝去或许又提醒我们:“我”与“我”之间永远有距离,舍“我”而求“非我”,只会失其本心而向消亡。
于是,庄周未曾说清,究竟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他选择一生徜徉于这段“距离”中,时而“我”,时而“非我”。有了艺术的飞跃又不致消亡。
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本来的那个人,亦真亦假,亦失亦虚,以那个“眼前的我”一颦一笑为载体,略施粉黛,在“我”与“非我”之间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