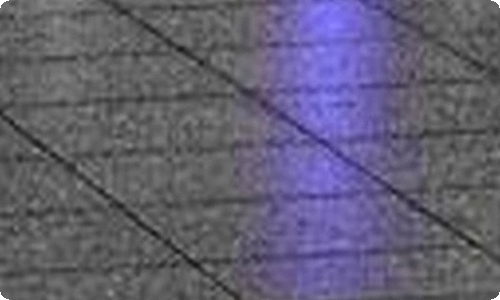我和父亲第一次聊起她时,我有些愤愤不平地抱怨道:“她自私自利、玻璃心、对人也很傲慢,但她呢…画画又很好,作文也写得蛮不错的…”
她呢,微微有些发白的南瓜脸上长着雀斑和少量的痘痘,眼睛像一个棕色的玻璃弹珠,头发上富有诗意般的缀上了一些头皮屑,像拉面一样垂着。
那天吧,天空诡异的没有一朵小小的,甚至是丝状的云彩。体育课上的她因为被人骂了一句,从开始到结束,整整四十多分钟,皱着眉头,充满了委屈,头发也怒发冲冠班立起来了。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不得不执行“朋友”的义务,站在她身边,看她像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一样,坐着给她的母亲打字。放学了之后,她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我们这两个“门神”也就被抛弃了。
凡是有人想跟她说说话,便会被她的一记眼刀吓得五脏六腑都在颤抖。有人是她不知什么原因划进黑名单,说一句话就要一块钱,两句话呢?翻倍啊,四块钱!对于她这般的政策,我们连一句话都不敢说,要是对她讲道理或指责她,她轻轻松松就把我们当仇人看。
一天,她生病,请假了。
空荡荡的后桌,我与另外一位朋友都觉得不自在,课间少了那位耐心教我画画的她,放学少了那位与我分享快乐的她,就如一片枯叶消失了原来的璀璨光芒。我常常劝说她不要太过内向,但这次,风吹过,真的会有她的身影吗?
第二天,她就出现在了门口。
我突然觉得她的自私自利、玻璃心和她的优点合并就是她作为一位“最佳损友”的资格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