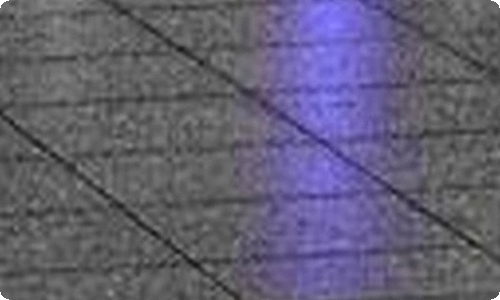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题记
母亲喜欢看书。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家,她最喜欢的就是捧了一本书,坐在长木椅上,冬天盖一被毛毯,夏天端一盏清茶,就那么津津有味地看着。她的手摩挲着光滑的书页,嘴巴无意识地微微张开,一双乌黑澄澈的眼睛倒映着洁白的纸和方正的宋体字,映出柔情无限。眉头舒展。
苔花一样的她,自由绽放。
一天,我在家翻箱倒柜地搜索“义卖”能用的物品。母亲探过头来好奇地问:“你要卖什么呢?”陈年旧物灰尘覆盖,呛得我直打咳嗽,我便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书啊,本子啊!”一边捂鼻皱眉继续翻找。听我的语气,她停住了,缄口不言。
听到书,母亲的眼睛又突然闪烁起来:“书?!……孩子,我有个请求,你能答应我吗?”母亲试探性地问我,像个怯生生的孩子。
我的直觉告诉我,每次她用这种小心翼翼的语气跟我说话,就是一定有什么极其严肃和认真的事发生。直觉驱使下,我不得不站起来拍落身上的灰尘,不带波澜地问她什么事。
她那瘦黄的脸颊似乎因兴奋而变得水润微红,紫黑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却又闭上,她像个羞涩的姑娘一样犹豫着。母亲视线投向一角,眼里迸出绚烂的憧憬。窗外阳光灿烂,一如她勾起弧度的嘴角。
“我想托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人卖《悲惨世界》。如果有,一定要帮我买哦!”
我恍然。母亲忙中偷闲,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大套《平凡的世界》,对雨果的《悲惨世界》早已“蠢蠢欲动”。母亲少年时,因为家里贫寒,外婆的脚重伤,她毅然放下了高中课本,担起了锈迹斑斑的水桶,撑起了一个家庭。然而母亲仍读书、爱书,重拾年少的梦想。沧桑岁月已过,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她眉间却有着苔花般青葱的光彩。书中有黄金屋,颜如玉。有穿过狭小人间后广袤的原野和浩瀚的星河,有放飞的理想与激情。我曾惊讶于母亲初中文凭为何文笔如此华美,原来奥秘在此。
又想起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我还在被窝里昏睡,模糊地听见一个含着笑意的声音,问我早餐吃不吃汤圆。再起床时,看见母亲小小的身影在厨房活动。悄悄跟上去看,她在烧一壶开水。水壶年代已久,盖子被水蒸气常年顶撞,已经盖不上了,必须有人压着,水才能烧开。母亲弯腰取出一个钢碗,盖在壶盖上,也不顾油渍污秽,紧紧按住,再松开,确保无碍,转身又忙碌铁锅。锅在火苗的热舞下烧热了,残留在锅上的水化作水蒸气。母亲拿着锅铲熟捻地铲出锅中的铁渣,甩到洗手池里,再挥铲,直至铁锅变得干净。铲出的铁渣还冒着丝丝水蒸气,升腾着,缭绕着,继而消融在空中。母亲青筋突出的双手在白白的水蒸气中活动,像揉皱的纸团,愈显得瘦弱。却又像苔花,不卑不亢,柔而有力。看得出,她在为我和父亲准备早餐。
苔花一样的她,无私奉献。
母亲在一家小工厂工作,她不懈地阅读,孜孜不倦地在汲取知识;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早早从被窝里出来为家人做早餐。她何尝不是那幽涧中自由生长的苔花呢?她微小,却能领略一滴露水之晶莹,一抹轻风之逍遥。她开的花也小,但素素妆、淡淡笑,我自轻盈我自香。被人所忽视,却不忽视别人,用自己的努力为世界点染一份绿意。
正独自感动时,母亲发现了我,朝我一笑:“你就等着大饱口福吧!”笑出了鱼尾纹,也笑化了我的心。
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