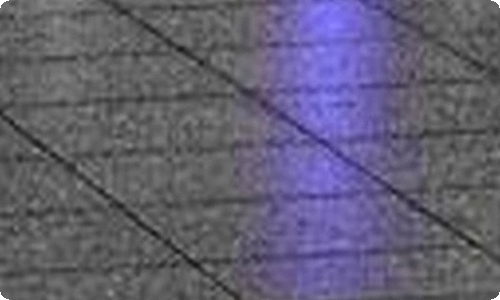儿时,对父亲的记忆总是不多的,仿佛也成了个可有可无之人。即使当下也早已明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对父亲的记忆似乎也只有这么几个了。
平淡无奇的夜,只有我与父亲度过。在我记忆里,那是一个不在母亲“管辖”下度过的夜晚,而父亲也外出了,我便统治了整个家。直到夜里11点,窗外不再有什么声音了,门口突然传来开门声。我赶忙合上书,关了灯,躺下。
我刚结束了我的动作,门就开了,在朦胧中,一颗脑袋探了出来,在黯淡月光下,看不太清楚,但从那佝偻的体态中已映出了无限疲倦。他又合上了门,动作是那般缓慢,仿佛夹在那棉花间,已消去了最后一丝声响。光在门缝里隐没了,我依然睡不着。
过了一会儿,浴室的方向有隐约的流水声,我在这份清脆中有了几分倦意。
约摸十一点半时,父亲才准备上床睡觉,脚步很轻,走到床边,停下,手似乎扶在了床垫上,有点吃力,床在微微颤动,他上了床,又想轻轻越过我,从我身上慢慢跨过去。那一刹那,我嗅到了父亲身上那浓重而复杂的气味:身上的一丝抹不去的汗味儿,薄荷肥皂的清香,那股并不生厌的烟味,不知为何,还有一丝我从未闻过的酒气。越过了我,他才一点点儿躺下。
可是,父亲躺下后,却仍不安稳,我仍记得奶奶曾说过父亲对酒精过敏,而今晚,他显然去应酬喝酒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却又怕惊扰到我。突然猛地抽搐了一下,迅速地下了床,脚步竭力的轻却因无力而凌乱了。接着他又跑去了厕所,一阵呕吐声,又过了几分钟,他才拖着虚浮的步伐回来,又是缓缓跨过了我,却因无力支撑而猛然倒在了一边。他无力地举起了手机,即使光只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我却看见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还有点浮肿,眼角还有一滴晶莹,是汗还是泪?我却从不相信他会流泪。
听见鼾声,已是三点多了,即使中间有无数嘈杂,他却是真正的睡熟了,才刚游离了现实的痛楚。
可是,六点,铃声准时响了,他又垂着昏沉的脑袋上班去了。
即使我与父亲熬了一夜,我却是全然无法体会他的痛楚的,他面对的痛是多少,又替我担下了多少,而我则是绝然无以为报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