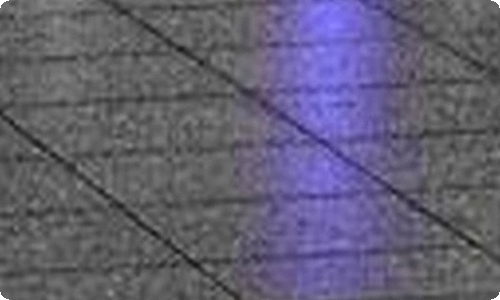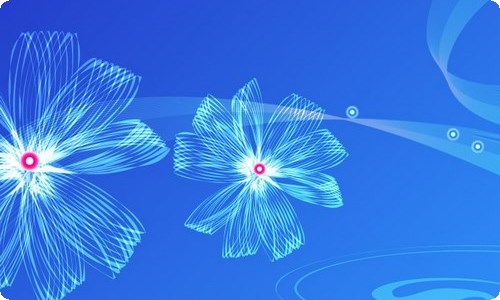
他,和他卖糖人的小车,蜷缩在夫子庙那个连光都没有的胡同里。
车上插满了用袋子裹着的糖人,但那些栩栩如生的图形在现在的市场上早已无人问津。飘起了雪,他停止了熬糖稀,把车移到一个小棚子下。
夜,很冷,几乎与他的心一样凉。
他在很多年以前,就是一个吹糖人的,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一个吹糖人的。那时的他多么年轻啊!在北京工作,推着车走遍大街小巷,走过亭台楼阁。那儿就像他的家一样,根扎在了那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请他吹个唐人。他一笑,随意扯一块糖,捏个洞,轻轻一吹,瞧都不用瞧,再摆个造型,一只龙就吹好了。把后面孩子激动地拿过糖人连蹦带跳,笑着跑回了家。
在那京城之中,无处不为他知,无处不为他晓,尽心劳作二十余载,却因北京租房价升高,迫不得已转来南京,离开了他视为母亲的长城与故宫……
如今,他在夫子庙最冷清的一个胡同里卖糖人,早上5点起,下午10点才能到家,就连这般早贪黑,一天连卖掉半碗糖稀都困难。每当他看到孩子们都兴奋地跑向对面的烤串店时,心里复杂了起来。
画外人易朽,谓琼浆半江美玉瘦,至高者清难朽,至贵春润因愁,松香接地走,谓青石流海连过东,既玄明不可量北斗,却何信小本买卖最轻松?
他顿了顿,思绪回了过来,发现糖稀冻住了,又开始重新熬。
夜,很长,夜,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