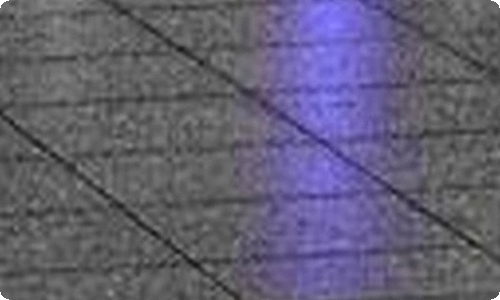冬天的湿寒从来都不拐弯抹角,却极是喜欢伸出手在人的骨子里边儿抓抓挠挠;风是大的,吹得院子里边儿的大树小树都直不起腰,却还是艰难地支着身,不愿与大地拥抱。
我们几个伙伴给驼爷寻觅了个没有主人的好地方给他住着,可是驼爷拒绝的义正言辞:“这不是我的,我可不好霸占别人的屋子。”
“那是没有主人的!”一个伙伴反驳着。
“那也不去!”驼爷涨红着脸吼道。
驼爷是我们院子里边儿的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驼爷的名儿是院子里头的伙伴们帮他起的,因为驼爷的背比骆驼的驼峰还驼,也因为驼爷不愿意把名字告诉我们这群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
说得好听些,驼爷是个靠着拾荒艰难度日的;说得不好听些,驼爷就是个靠着捡捡垃圾,收收破烂来糊口的。
驼爷老,他脸上那皱纹记录了岁月,记录了光阴,被阳光和风雨拍打着,刻进了他沧桑的面颊;驼爷老,走路时生涩粗噶的摩擦声会从他高大却瘦弱的身躯里传出来,就像年久失修缺乏保养后被迫重新上岗的机器一般。
他是生了锈的,可没人愿意给他抛抛光,上上油。
驼爷住在楼梯下面低矮狭小的空隙中间,他总是很委屈他高大的躯体,把这躯体蜷缩在堆满了纸板子的阴暗角落。可无论如何,驼爷都不肯去我们寻着的“好地方”。
“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的,又不是讨饭的,要什么施舍嘛。”驼爷这么对我们说着。
他的脸色不大好,不知是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还是害了病。
一天后再次见他,我看到他的背更驼了,就像是直不起腰的老树。我和伙伴们远远望见一个约莫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在鄙夷地对他说着什么,旁边几个年轻人一边笑,一边叫好。他们的声音像嘶吼的公鸭和岔了气儿的喇叭,吵吵嚷嚷却不以为愧。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我一定要去伸张正义!”一个伙伴恶狠狠地盯着那一群年轻人,一边坚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目光是火,我猜那几个年轻人已经被烧成灰烬,随风飞舞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带着把几个年轻人挫骨扬灰的决心走向驼爷,正准备和这几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来一场殊死搏斗时,驼爷拦住了我们,给几个年轻人赔着笑:“嗯嗯,好好好。”
年轻人们趾高气扬地走了,留下我们空空地摩拳擦掌。我问驼爷:“他们谁啊!我要去捏爆他们的脑袋瓜瓜!”
驼爷只是一边摆手一边叹气,也许是叫我们这群气盛的孩子不要参与到这俗世纷争里头去。我们气愤于驼爷的忍耐,一边踢着地想把怒火转移,一边嘟嘟囔囔地走了。
驼爷的抽气声断断续续地从我背后传来,好似小猫儿不满的嘤咛,却少了几分抱怨和几分生机——只可惜我在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这声音之中的绝望与悲伤。
院子里嘴碎的大姑大婶开始传起了驼爷的悲惨往事:他最宝贝的儿子把驼爷给自己养老送终的房子骗去了。那日嚣张的年轻人,大概就是他的儿子吧。
最后一次看到驼爷,是他直板板地伫立在院子门口,当我和伙伴们走过时二话不说地将几包糖塞进我们怀里。糖是进口货,贵得很,爸爸妈妈都不愿意给我们买。
“你花这些钱干什么啊?”我们疑惑地问驼爷:这一包糖的价格抵得上驼爷两周的饭,如果我们吃了糖,那驼爷该吃什么呢?驼爷不回我们,僵僵地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那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过驼爷了,问为什么的时候大人总是闭口不提。只有走到楼梯间想看看驼爷时,会被多管闲事的大姑大婶一把拽开,嘴里不停地咒骂:“晦气,晦气。”年长一些的伙伴好像知道了什么,却也是不说,我却能感觉到空气里弥漫的悲伤。
如今我才明白,原来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受过了生死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