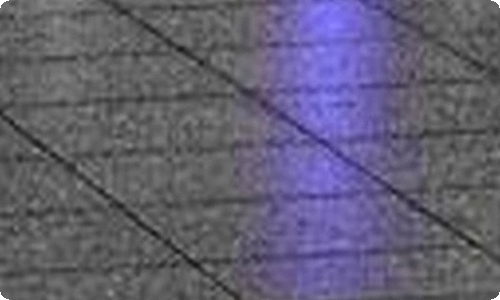我们家常吃黄奶奶的菜,我也经常去买。她摘,我拿,我们一边说着闲话。
据她讲,她的腿曾经中过风,老伴的也是,上了年纪后,身体都不好,自然也挣不来钱,现下只能靠种菜换钱度日。
八十多岁了,我还经常看见她在一大片菜地里忙碌着:担水、锄地、拔草……灰白的头发上沾染着经年洗不净的泥星儿,细瘦的身躯佝偻着,就像一根压弯的枯枝,随时都会折断似的。
她种出来的菜,一小部分自己吃,一大部分卖出去以求换点活命的钱。
有一年正夏,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嚎叫着,发着令人烦躁地叫声,像是在替烈日炎炎呐喊助威。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大地上没有一点风,植被们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快到饭点时分,我的母亲看了一下冰箱,没有鸡蛋了,于是自然想起了黄奶奶,便给黄奶奶去了电话,问还有没有鸡蛋卖,她说可以卖给我们二十个。母亲听了后就说,现在不急,有时间就开车去拿。
半晌,听见敲门声,我去开门,门外竟是黄奶奶,她的脸上满是汗水,大口地呼着气,手里提着一袋大鸡蛋,瘦小的身子与笔直的门框相衬,显得更加弯曲了。母亲惊讶地说:“黄奶奶,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我去拿吗?”“你忙,我给你送送,也不花太多力气。”母亲忙给她端了一杯水,她喝了几口水,就和母亲交代,“最上面的那个是双黄的,天热,蛋要放进冰箱……”她刚说完,母亲就拿来一百块钱给她,“不用一百,一个蛋一块,一共二十。”“那比超市都贵了。”最后,母亲硬是把一百塞给了她。她走之后,我便把蛋放进冰箱,数了数,竟有三十个。
她是很老实的。她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她大概压根儿都没想到这点。
有一年的三月三,春风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地由上到下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人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那天我正在写作业,黄奶奶来我们家,端来一锅不知名的野菜里面还煮着几个鸡蛋,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节气,要吃“地菜煮鸡蛋”,母亲忙给她拿钱,她忙说:“我不要钱。”然后就赶紧走了。
一天,我们家去黄奶奶家买菜,我们把菜篮子给她,她就去地里拔菜,结果拔完菜往回走时,她的身躯突然绷的笔直,然后身子一倾,像是一根离了地的木条,摔在了地上,我们赶紧把她扶到屋内,她切切察察地重复着她没事。
晚上,当晚霞消退之后,天地间就变成了银灰色。乳白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像是给墙头、屋脊、树顶和街口都罩了—层薄薄的玻璃纸,使它们变得若隐若现,飘飘荡荡,很有几分奇妙的气氛。小蠓虫开始活跃,成团地嗡嗡飞旋。布谷鸟在河边的树林子里,用哑了的嗓子呜叫着,又不知道受了什么惊动,拖着声音,朝远处飞去……我去黄奶奶家看她,一进门,没看见黄奶奶,却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收拾衣服。
“黄奶奶呢?”
“住院了。”
“为什么?”
“骨头摔断了。”
我没有再多问。
回到家之后,看着那些还没有吃完的菜,眼前总是浮现出了她的样子,心中升起一丝愧疚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