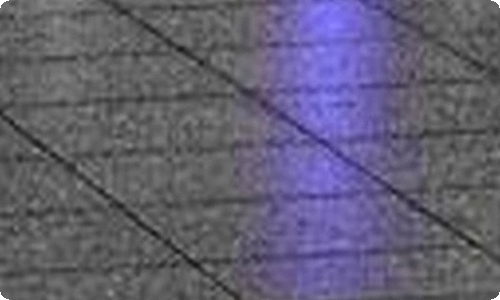我不是擅长种花的人,却格外地爱花,觉得夏季开的花尤为灿烂。
五六岁的夏天,太阳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更燥热,更狂放,毫无愧疚之心地点燃了大地。我终日随爷爷一起,白天摘些野蘑菇,入夜便听他讲几个老掉牙的故事。
爷爷爱花,在阳台上的花坛里侍弄着些石莲、翠兰之类耐活的花草,一些精致的花盆里还栽着几株夜来香或太阳花一类。我不曾涉足过花的世界,对这一切自然好奇,也摸索着种花之法,在纸杯里插上一棵翠兰,不想那植株适应能力超凡,生了根,在小小的天地里活了下来。
玩耍的间隙,我捧着花,咿咿呀呀地唱着不成调的歌谣,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蹦。一级,两级……盛夏的太阳在日暮时分竟然除去了泼辣,捎带上了一丝温柔。
爷爷靠在一把藤椅上,和他那缠满了胶布的老伙计一起,在天边的最后一丝余晖里望着檐上吵闹不停的燕子窝。有时会忽然从身后抽出一本书页泛黄的《西游记》,考我开篇里讲了无数遍的四大神洲。
这便是我与夏天,也是与花的初见。
人注定是要长大的,这也代表注定抛弃一些儿时痴恋着的梦话。我的童年就那样过去了,但长大的我仍是爱花,爱夏天灵动的太阳花,甜美的夜来香,以及难得一见的夜昙。
昔日在小纸杯里发芽的爱好,如今也到了盛开的地步。我种花的技术进步了不少,除了市场上现买的华丽花卉,自己也认真栽种了几盆常见花草。闲暇之余,我仍会在暑期短暂的夜里到阳台上转一趟,拨弄几下花叶,瞅瞅晾在绳上的衣服,轻轻地哼两句白天听过的歌。
一天晚上,我又朝阳台走去。夜来香安静地开着,清甜的气息为月光披给阳台的白纱洒上了最自然的香水。一只灰褐色的扑灯蛾蛰伏在花盆边缘,似乎忘记了飞向屋内黯淡的灯光。我不盲猜它是否被花香迷醉,但是已确定自己遭夏夜微凉的风和微醺的香魅惑,不愿离开。
我隐隐约约听见爷爷在里屋读着什么:“话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下分为四个神洲,这四个分别是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芦洲。这东胜神洲海外有个傲来国……”我的思绪也随着这声音渐渐飘散在花香里了。我回忆起自己幼稚的小小身影在门前的空地上跳台阶,唱歌,昏昏欲睡地听爷爷从花果山美猴王讲到三打白骨精,最后被问起讲了什么,只迷迷瞪瞪地哼唧两声:“孙悟空……”便倒头做了梦去。
夏天的花勾走了我的魂魄,我醉于它的美好,同时却忽略了一些记忆中重要的东西。
前不久老师忽然布置起练字任务来,虽然少不了抱怨,我还是找出一本字帖,规规矩矩地练起字来。突然,我的笔尖停留在一句话上,“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花,这个词仿佛一把钥匙,令我又忆起了那一连串的故事。我突然很想爷爷,也突然知道了自己忽略了什么。夏天的花永远美丽动人,在一片片花海里,我也由最好的童年走入最好的少年时光,可我似乎忘了有一个始终站在花丛外的老人,同夕阳般垂暮,静静地望着我的欢乐,眼中闪动着无尽眷恋。
夏天的最好时节是七月,阳台上每年都盈满香气。我却只愿带着几缕花香,如童年那时一般伏在爷爷的藤椅扶手上,回答他无数稀奇古怪的问题,让夕阳的光芒透过阳台上的花,为我戴一顶灿烂的编织帽,也为爷爷披一件镀金的外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