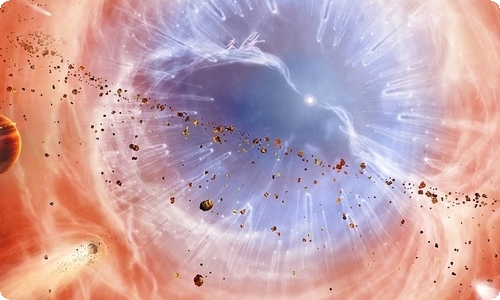老六是我在复读期间的一个舍友,全宿舍属他年龄大的,但是因为来得晚,排行只能垫底。临高考前的一天,哥几个晚上睡不着说起老六来,最终大家的意见很统一:老六其实是个下凡的神仙。
老六来的前一晚,宿舍里商量要给新来的一个下马威,具体的实施方案无非是些敢说不能做的扯淡主意,断断续续的商量了一个多小时,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的老大实在忍不住了,阴沉着脸挤出一句,“都别搭理他。”当烟雾飘到老大脸上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一部电影——《教父》。
初来乍到的老六像只受惊的大雁,抱着他的铺盖卷,穿着棉袄棉裤坐在上铺,双腿耷拉在床边,来回晃动着,他对面的我看着两条犹如钟摆一般的腿,心慌的厉害,好像是高考前的倒计时。他的下铺三儿终于忍不住了,甩甩头发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蹦到地下,我还以为这就要打,没想到老二盯着他脚看了半天没说话,又坐到了床上,隔着那两条钟摆朝我挤眼睛,然后捏着鼻子做呕吐状,我领会了他的意思,和他一起坏笑起来,我们两个笑声越来越大,让上铺的老六很诧异,两条钟摆不动了,瞪着他铜铃般的眼睛诧异的看我,我也寻着这眼神看他,他却慌张的避开了。他有个标准的瘦版国字脸,留着极短平头,远处看就像是一块立着的板砖上又刷了一层平整的黑油漆,在这块板砖上长着一个硕大的鼻子,那鼻子像是一个人被逼到墙角,另一人一拳打过去把它打的向两边平摊。由于他的鼻子实在是扎眼,没等我欣赏完,老六又回过头来,发现我还在看他,他干脆把头扭过去,整理他的铺盖,我自讨没趣的拿起一本牛津大辞典胡乱翻页,但是老六的一举一动甚至是挠挠头我都觉得是一出好戏。对床的老二调侃我说,“小午,你看这本书折寿。”我刚要反驳,老六傻笑着转过头看着书说,“这本书三十八,我不舍得买,到时候借我看看啊。”说完又一阵傻笑,我朝他呆木的点点头,他继续回头整理床铺。这是老六来宿舍的第一句话,让我心里酸酸的。
这句话一下打破了老大的计划,很久以后老大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老六才是老大啊。”我们看着老大的表情,都觉得跟错了主子。慢慢的我们和老六熟络起来,用我们的话说,老六其实很“开放”,不是刚来那会的一脸严肃。一般我们说什么老六一定会插上一句,或是句很傻的回答,或是一个无聊的疑问,都能让我们讨论的热火朝天。有时几个哥们在一起讨论学校里的那个女孩更漂亮,老六都会选择回避,或是去厕所,或是去阳台。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老六不是同性恋就是早有了女朋友。直到一天,老六晚上说梦话,只听他断断续续的念叨,什么大蒜涨价了,家里麦子该收了,我正给女朋友发短信,听到这里不断窃笑,突然老六突然冒了一句,“红……”大有意味深长的意思,我像打了鸡血一样,试图摇醒对床的老二,没想到老二早就捂着肚子笑成一团,环顾四周,全宿舍都躲在被窝里窃笑,被子随着他们起伏的身形不断颤抖。第二天起来,我们几个殷勤的帮老六端脸盆,拿洗面奶,老六受宠若惊的拿着洗面奶说,“哎呀!这是什么啊,没用过啊!”又是一阵傻笑,和昨晚的意味深长判若两人。他一傻笑我们也跟着傻笑,最后老大憋着通红的脸问他,“老六,说!红是谁?”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老六一点也没怂,好像“红”就是一种颜色,没有其他含义。“什么红,不知道啊。”我们几个丝毫不放过他继续逼问,结果气的老大说他上去六十年要是被敌人抓去,肯定是个好党员。然后又指着三儿说,“不像你!文革时期棉裤裆!什么事到你嘴里全说出去了!”三儿一脸委屈,等到宿舍人走的差不多了,偷偷问老六,“喂!红是谁,你要说了,我就请你吃饭!”结果我们的宝贝老六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啊!”只留下干瞪眼的三儿,老六抱着书乐呵呵的出去了,三儿却扑哧一声笑了,骂了句“这混蛋口风是严。”至今老六的“红”依然是个谜。
老六不管在哪口风都严并且低调,但是他下床却很张扬,他从来不踩着小梯子顺着爬下来,而是单脚一点梯子,双手撑住床,身体向前一冲,双脚“咚”一声的砸在地板上,这一切总是发生在眨眼的功夫,从未失手,老四是个运动健将,对他的这套功夫羡慕已久,总是趁着老六没在跟前偷偷练习,有一次,老六做值日,刚拖了地,地板上的水还未干,趁老六放拖把的功夫,老四从床上一个箭步,跳在地上,同样是“咚”的一声,然后“嗖”一下就滚到对床的床低下,疼的直骂老六,老六从厕所出来,看到车祸现场一样的惨状,伸手去扶老四,等老四摇摇晃晃的起来,老六说,“以后什么都要注意啊。”老六很严肃,老四本来想骂他,看到他一脸严肃,就没了下文,我一眼抽出了老六不对劲,这次我们没有逼供,是老六自己说的,“我的饭卡丢了,一百多。”我们赶紧问然后,老六笑着说,“找回来了。”我们都骂老六欺骗感情,作势要打。然后老六笑呵呵的爬上床,不说话了,我们五个像仰望领袖一样看着他,琢磨他刚才一点也不傻的笑,老大往前一站,深深地说,“老六,要是有人欺负你就和哥儿几个说。”说完给自己点了颗烟,坐回床上。老六没说话,用被子蒙着脸,过了一会儿,老六在被子里后吼了出来,荡气回肠的,我们被吓了一跳儿,三儿从下铺坐了出来,看着老六,我把老六的被子掀开,老六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喘着粗气。
晚上我们宿舍出奇的安静,没人想说话,也没人敢说话,我们都睡不着,捧着书瞎看。大约一两点,我想给老六发条短信,我和他关系还算好,本打算问个明白,等我拿出手机来才想起老六压根没手机,于是写了张纸条,扔到他床上,过了一会儿,纸条传回来了,上面除了两个“谢”字,什么也没有,我一脸无奈,准备放弃,老大咳嗦了一声,我知道这是老大让我继续,于是我和老六就传起了纸条,就借着走廊上的的光,一个纸团不断地划出银色弧线,其实那天晚上我猜老六听懂了老大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出来,依然是用最原始的方式低调的告诉我,捡到饭卡的人找到了,那个小子逼着要好处费,结果没给,那小子就打了他脸一巴掌,然后还骂他是个乡巴佬。四点了,哥儿几个都没睡,疲惫的老六却先睡了,我把事情告诉其他人,三儿吆吆喝喝的要找他哥给那小子挑了脚筋。老二胆小也说怎么着也要揍他一顿,老大还是最后一个说话的,“咱们欺负老六行,别人就他妈的不行。”不得不说这句话至今让我震撼。
一个星期后,处分下来了,我们几个人被学校记了大过,黑锅全是老六抗的。晚上老六却像庆功一样买来啤酒,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老六说老师很宽容,原谅了他。然后老六声泪俱下的感谢学校,感谢党弄得我们一阵恶心,我对老六说,“你就不感谢我们,可是我们打的人。”老六傻笑着说,“全宿舍就属你学习不好,别成天鼓捣着写诗,多看看课本,小心你文化课再考个二百六。”我仔细看着老六第一次觉得这笑一点也不傻,像个长者。
高考结束,老六差几分上山大,去了一个普通的二本学校,后来一起吃饭说起这事来,我们都为老六可惜,而他却依然那副德行的劝我们,“没事,这二本拿钱还少点,看,这不置办上手机了。”他这句话,把我们说的直低头吃菜,三儿眼里泪直打转转,拿起酒杯咕嘟一口干了,对老六说,“还是老大那句话,咱们欺负老六行,别人就他妈不行!”说完把酒杯一摔,颇有壮士一去夕不复还的劲儿,老大皱着眉头笑,“你小子喝多了吧!”老六故作惊讶的对老大敬酒,“哎呀,这可是第一次见老大笑啊!以前不知道啊!”说完我们都闹起来,满脸横肉的笑着,拿起啤酒全泼到老六身上,老六躲在角落里边挡边傻笑。闹够了以是凌晨,六个人在大马路上抽风高唱国歌,经过复读学校的时候,我们对着学校门口齐齐的吐了口唾沫,好像吐出了一年的所有怨恨,看着唾沫划过天空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其实最苦的复读也就那么回事儿。
现在时常还会想起那群没心没肺的人,特别是老六,不知道他有没有让人欺负,昨天给他打电话,听他一开口,自己就先哭的稀里哗啦,我哭了十分钟,他听了十分钟,然后我对他说,“六哥,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