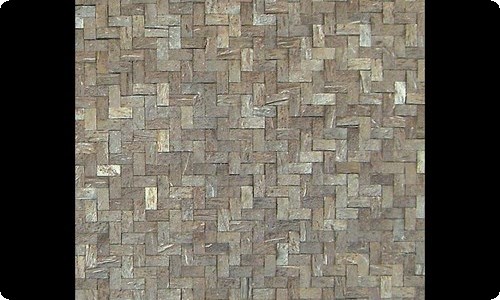寒假,我细细品读了汪曾祺先生的一本著作《人间有味》。汪曾祺先生似乎对四方美食有一种执念,他对美食的热爱与追求是令我敬佩的。
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汪曾祺先生为《学人谈吃》作序。学人是会吃且善于谈吃的。学人可以是大学教授,生活相当优裕。但他们却极少吃富油水的食物。教授们有家,有妻儿老小,当然不能这样的放诞。文中还有一种人,叫“准学人”——学生或助教。这些准学人两肩担一口,无牵无挂,有点小钱,他们倒是能偶尔一吃昆明的一些名菜了,如“培养正气”的汽锅鸡、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甬道街的红烧鸡……
在汪曾祺先生眼里,学人是无须吃得山珍海味的,但一定是会吃且善品味的。学人所做的菜大多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而我以为“学人”当以苏东坡为最。
苏东坡好吃,于他诗文中常见美食。他在《初到黄州》中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写《煮鱼法》,细致入微,先放什么后放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做《东坡羹赋》《菜羹赋》,强调“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不用鱼肉无味,而有自然之甘”。用蔓菁、白菜、萝卜做的菜粥,能吃出“自然之甘”来;他在《论食》中说:“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郡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脍。即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更是将自己的饮食之乐与美文融为了一体,让人读之就垂涎三尺(其实是我自己)。
其实汪曾祺先生也算得上一位学人,他与苏东坡先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经过波澜四起的生活,千山万水的历程之后,再吃到童年的那股熟悉的味道,如汪曾祺、苏东坡这般细腻的人,不知心中泛起怎样的涟漪。
若将学人说的通俗些,便是吃货。而吃货的基本技能,就是什么都看起来很好吃。有一年,汪曾祺先生去草原林区体验生活。六月的草原绿油油,开满了黄色的金莲花。他很兴奋,当即作了首打油诗:“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而上一个遇到美景却满脑子是吃的人,则是苏东坡。他写春天是:“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他们吃东西是会思考的,是极富想象力的。
爱吃的人,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汪曾祺先生一直念念不忘云南的菌子。在昆明住了七年,四十多年后仍然忘不了,还能在文章里一一数遍鸡枞的难以比方的味道,白蘑煮成的鲜汤,还有各种长得奇形怪状的菌子。这样的“吃货”使我同感,他不是“酒肉穿肠过,味道全不知”的人。汪曾祺先生的舌尖一定是有记忆的,他会记住那些让他喜欢、感动的味道,亦使我喜欢、感动。我觉得,这样的吃货,才能真正谈得上爱美食,懂美食。
所以,当汪曾祺在离乡几十年后,在沈从文先生家再一次吃到了茨菇炒肉片后,从此又有了感情。其实,终其一生,汪曾祺先生的味蕾都在追寻儿时的味道。
他只是写了两句话:“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读懂这两句话。
食道旧寻,寻那儿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