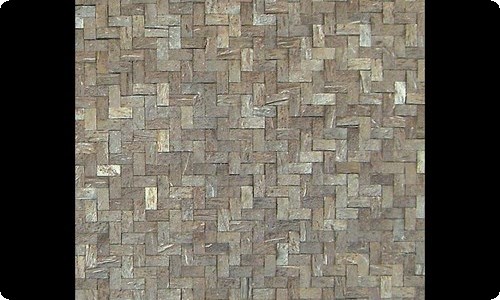越飞越远的纸飞机,越飘越远的小纸船,都满载着儿时的惆怅,淡出了我们的记忆。
——题记
抚过封面,一缕一缕麦杆黄的云霞,慵懒地飘在莲子白的空中。云层下面,一个女孩儿坐在屋顶灰蓝的瓦砖上,晃着脚丫,吹着泡泡,充满了童年的散漫;旁边的一个青年望着天空,若有所思。这是弄泥和阿唱们的故事。
阿唱是精神病患者,但不代表他们就是疯疯癫癫的傻子,他们只是把自己关在了过去。喜欢画画的阿唱,高考失利的七妹会默写课文,喜欢弄泥美术老师的阿布,爱说大话的胡清虎只是个希望得到父亲和大家认识的孩子。他们的出现,为弄泥的童年再次增添色彩,弄泥也因他们的出现而开始成长为一个懂事的姑娘。
我不禁思绪飘散到那个黄昏深处、暮色掩映的小屋。
小屋的主人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笑起来满脸皱纹,如绽开的菊花一般,很可爱。那是个宁静的午后,我与对门的小伙伴趁家里大人午休,偷偷溜出去去田里玩耍,田野里有的只是流水潺潺的小曲与知了声嘶力竭的长鸣。我们见树上的荔枝都熟了,外衣红艳艳的,个头很大。便提出要上树摘几个尝尝,乡下的孩子没有电子产品可以玩,摸鱼、爬树都是小意思。我麻利地爬了上去,正要去摘,没抱住树干,手一滑,从树上跌了下去,手臂和膝盖都擦伤了,血汩汩地往外流。这时,不远处的小屋门开了,一个身着蓝碎花衣的老太太拎着木棍往我们这里走来。小伙伴吓得面如土色,赶紧跑了,留下我一个人。正当我要爬起来时,老太太却已走上前,我以为她一定会狠狠的骂我一顿。但没想到,她轻轻地抱起我,走向她的小屋里,在屋里摸索出一个医药箱,先用清水清洗我的伤,再用碘伏轻轻擦拭。其间一言不发,我静静的看着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为我清洗伤口。全然忘记了伤口的痛,院子里的阳光从门槛边射入小屋里,照在老太太的有些粗糙的手上和我的膝盖伤口上。消毒完后,她问我:“你是哪家的小妹,怎么跑到这了,这是爬树摔的?”我点点头,并小声的回答了她。这个老太太真温柔,我想。她也不责怪我,而是从他家厨房里拿出一小篮荔枝。我因为偷吃荔枝,不敢吃了,但她却笑了,像一朵秋日里的菊花一样温暖。吃吧,今天刚摘的。说着播了一颗递给我,白花花的果肉实在太吸引人了,我也就接过,狼吞虎咽下这些荔枝。老太太一直笑着盯着我,一颗也没吃。年幼,不懂得照顾别人。对于那天记忆,也只剩下甜津津的大荔枝与老太太和蔼的笑靥。下午,父母来找我了,一直给老太太道歉,老太太一直是笑着的。
后来我常常去她家玩耍,在她家不光有荔枝吃,还有小人书,老太太还会教我折纸飞机。很简单,纸飞机飞出手时,我看着它飞向前方,虽不远,但却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她折完后总会递给我,给我去把玩。有时飞机一头扎进田里边,再也寻不见了,我怕其他的纸飞机也会消失不见点,收了起来。待在老太太家的时光总是美好的,但也是短暂的。眨眼间,蝉叫累了,水流不动了,荔枝也过季了,我也不是原来那个几岁孩童了,背上书包去到没有荔枝树的市里读书了。
有一个秋天,路过田间,熟悉的小屋老了,它的主人也老了。门前一堆人在哭着烧纸钱,家里人告诉我,老太太在一个黄昏走了,我心里愕然,空了一块,满是弥补不了的惆怅,我爬上顶楼,从小木盒里取出几只泛黄的纸飞机。我在小院里一个人默默地把他们烧了,我看着它们化为青烟,希望它们能在天堂上好好陪着这位老太太。还有一只纸飞机,上面画着荔枝的图案,我站起身,用尽全身力气将它投向了万寿菊黄的天,望着它远去的方向,我想起了那笑起来像菊花般温暖的老太太。梦里那位老太太朝着我微笑,她已抱不起我了,我与它拥抱着,手里攥着那只画的荔枝图案的纸飞机。
一周后,我在回家的路上,见着家附近一棵荔枝树,树叶稀稀拉拉的,很丑。扭曲的枝干间是一只带着荔枝图案的纸飞机。我的泪湿润了眼眶,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的手里。
书中的弄泥的童年还在继续,书里的那些小伙伴还站在童年的门槛上,朝我微笑。他们和我一样,那么纯真而美好。我的童年呢?它已经停在泛黄的纸飞机上了。萤火虫的小宫灯做着梦,梦见另一个夏夜。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