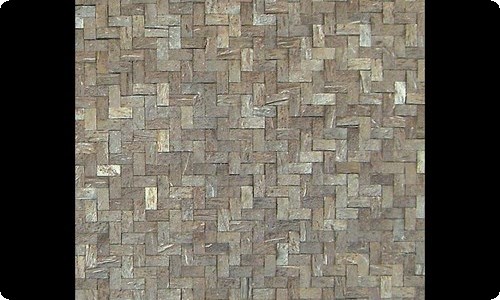读书之意义有二,其一者悟前人之思想。文以载道。又曰:文如其人。屈子高洁,故其辞亦高洁;太白疏狂,故其诗亦仙逸。太史公能传千秋,陶潜能闲万世。因其境界者也。
思想各有异。中华数千年之思想,于文学与水墨画中可见一斑。何谓?追求境界者也。水墨画,寥寥数笔,形离而境界全出。古文亦如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寥寥数字,景象全出,境界神矣。西方文学类之于工笔、油画,追求形似。现代之萧红《火烧云》,此形彼状,描绘甚丰,而读者据其想象。所想所得仍是萧之所描所绘,即有超出,模仿而已。思品示童以一米线等现象,亦似工笔画,以此为戒,然其所识则为各现象,如后新状现,何以类?况所记亦有所忘,行之远忘之疏矣。莫若中华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水墨画。何以为礼?类之生矣。以此为纲,行之愈远,行之愈深,必无所越。
另有一支,即日本动漫,二者兼而有之。
读书既多,素养渐成,益近于境界者也。所谓知书达理者也。以书践生活,则现实之一草一木皆著理想之色彩。如能以此观世界,如此待万物,则积蓄丰,虽一草一木皆文章。如不能以此观世界,则积蓄穷乏,纵乾坤倒转亦只知尖呼耳。
积蓄既丰,则流沛且长矣。艺之生也。所读之书必左右其艺。常观油画则思描思绘;常观水墨画则思水墨传神;常观日本动漫,则思光影波动。
如今之读书偏此道矣。一切皆为应试得分。而表露亦如此。八股灭而再生。立一主题,后则杜撰以证之。如表达“母爱”,常以雨中送伞,病中送诊为证。文坛之以表达技巧杜撰故事以感动、启迪之类靡漫。论文亦如此。要求于各行各处,然所积穷乏,故“天下文章一大抄”。吾甚厌之。然亦未能脱身于外。悲哉。
如我辈能褪伪俗,行本性于自然,直击境界,理想之于现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