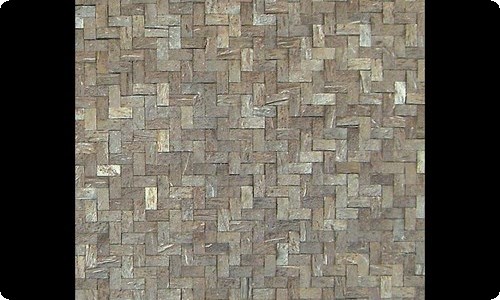死亡向来是中华文化所避讳的话题。季路曾问孔子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不信鬼神,专注于人世间的事物,不把注意力放在死后,其本质是对死亡的回避。周国平说:“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一语道破中西哲学分野所在。
哲人与诗人不同。诗人往往直抒死之悲哀,发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感慨。哲人不满足于此,较之悲叹,他们更希望通过理性剖析死的本质。对于他们来说,要排除死亡的困扰,不能靠抒情,而要靠智慧。所以,凡是对死亡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无一不试图规划出面对死亡正确及理智的态度。当这种态度被构建得基本完善,也就成了一种思想。
例如功利主义。它主张追求“最大幸福”——既然死无法避免,就不必去考虑,重要的是好好活着,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最明智的态度。伊壁鸠鲁说:“死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死尚未来临;死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因而死与生者和死者都无关。”他提出,我们应当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享受人生的快乐。中国儒家学派尽人事、听天命的主张亦属此类。总而言之,重生轻死,乐生安死。这样理智的现实的态度为多数哲学家所倡导,也易于为一般人所接受。
上帝是公平的,他在人出生之时赋予他一切,最后又差遣死亡将其全盘夺走。任何人免不了一死——这常使人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安慰。假如情形倒过来:人皆不死,唯独我亡,那他一定会觉得很不公平,痛苦会因嫉妒和委屈增加数倍。除了英雄主义的自愿牺牲,共同受难比单独受难更难以忍受。人的灵魂被平分成两半,一方面,他渴望永生;另一方面,他又迫于终有一死的肉体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少的君王都曾寻求过“长生不老药”,想以此达到永生。
那永生是否值得向往?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被最早沉思死亡问题的哲学家漏过。卢克莱修说:“我们永远生存和活动在同样事物之间,即使我们再活下去,也不能铸造出新的快乐。”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一个人在此时或几千年后看到的同样事物,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天下将不会有新东西,永生不值得向往,且是荒谬的。
死亡像太阳般不可直视。然而,即使扭头不去看它,我们仍然知道它存在着,感觉到它正步步逼近,将它的可怕阴影投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死亡迫人思考,因为它是世上最确凿无疑的事实,它不可避免。但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又会觉得不可思议——人人都会被投下这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怎能让人无动于衷呢?人生的终点是死,而死又意味着生前意志的绝对虚无,那人生岂非是虚无?是,也不是。对于历史,个人的意义接近于无;但对于个人,历史的意义也接近于无。在历史面前,个人何其渺小;在个人面前,自我却是一切。
如果能像功利主义那样不去想死亡,或是把它当成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倒不失为一种准幸福境界。遗憾的是,这一点除了愚者及历尽沧桑的智者,很难做到。一个人如果曾因想到死亡而感到真正的绝望,他的灵魂深处从此会留下几乎不愈的创伤。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太习惯了,对于死却很陌生。想想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活着,从未死过!人们常把死亡比作是无梦的长睡,以此安慰自己。可两者区别一目了然:酣睡的痛快在于醒来后感到精神饱满,长睡不醒,还有什么痛快可言?
像死亡般的无感状态绝不能说是幸福。世上一切美好,都是以有感觉为前提。人之所以恋生,正是因为活着能感受到周围世界带给他的各种感受。人之所以厌恶死,也是因为死剥夺了他感受这一切的可能。死不是长睡,而是永远不在场。
死亡是个体意识的绝对毁灭。倘非自欺欺人,从中绝找不出正面的价值来。然而,思考死却有价值。它能让人以超脱的心态面对世事。
向死而生,生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