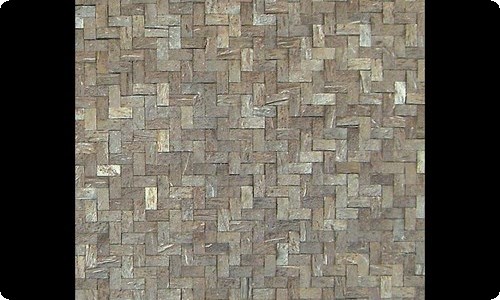我与世界相逢在镜中,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一点轻蔑。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唯一的灯。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敌。
——题记
1960年1月4日,大雨滂沱,时年47岁的阿尔贝·加缪死于一场车祸。此前,这位诺奖得主曾不无戏谑地讲道:“在我看来,没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了。”造化弄人,天命无常,加缪之死为他所提出的荒谬推理添了一笔沉重的注解,同时也向世界宣布了其永久性出局终极选择。
被罗兰巴特誉为“零度写作”之鼻祖,《局外人》凭借其独到的旁观视角和大量运用的白色书写的直陈式短句首次突破了古典主义写作的局限,开荒诞创作之先河,实为一“文学史上的重大时刻”。用简洁枯寂的文字写人,以深沉婉转的笔调写景,有一种形而上的悲悯与愤怒洞穿了整个叙事,若隐若现的黑色幽默掺杂其间,更加突显了局外人的意识与社会的逻辑间的冲突与缠绕。在小说中,从惊世骇俗的开头到离经叛道的结尾,接二连三发生却毫无然联系的死亡事件,都给人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有关这种荒谬感,我要在此强调的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全然由此而生。
麻木近乎冷血,任性近于天真,对于主人公默尔索这类人物,我既谈不上喜欢,也不至于憎恶。我一直只是把他们当作某种局外人的悲喜剧来看待,以至于啼笑皆非。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默尔索并非邀名射利之徒,也根本不屑于巧言令色或是附庸风雅。他有时与人虚与委蛇,但这些都只不过是疲于对偏见的应付而已。他是个真实的人,这一点在小人物中实属罕见。“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文章经典不亚于《百年孤独》开篇的首句令我想到了《庄子至乐》中一段相似的描述:“庄子妻死,方箕踞鼓盆而歌。”无情的极处便是至情,默尔索有着庄周的飘逸,却少了孔丘的克己复礼,并且因此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你到底爱不爱我?”当玛丽把这个问题扔向默尔索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个疑问句而是某种恋人间乐此不疲的语言游戏了。可默尔索拒绝这个游戏,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以他仅有的对真实和绝对的激情。
卡夫卡的人性理论说:“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默尔索弃世,但他毕竟缺乏博爱济世的上帝情结。而他的厌离也并非出于对逐求的不满。厌倦机械生活行为的结局,是他开启意识活动的序幕。马上,默尔索开始以一种意向性的目光审视世界。然而如萨特所言,他在偶然中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意识,却又被强力驱逐到“刺眼光线的干燥尘埃”中去。胡塞尔说:“人被粗暴地驱赶到自身之外。”世界的观念无处不在,以至于无孔不入,人类的意识内部却往往存在空洞。在海滩上,滥施淫威的太阳变成了维护法度的日神阿波罗,来自理性和秩序的强大压迫感迫使着默尔索叩下扳机。
安德烈。布勒东在其评论中说:“变节者科尔里奇在一瞬间看到了世间的真相,然后闭上了眼睛。”进入监狱后,默尔索也有相似的经历,但他并未因此回到精神上的安逸中去。他的生命于是终结于俄狄浦斯般的逃避与抗争。在星光与缄默的夜,他于未来死亡的深渊中了解到了一点,那是库切在《耻》中借女儿之口说出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更高层次的生活。”
加缪塑造默尔索并非没有目的,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是其中之一。从伊甸园被放逐至人间,人类仿佛是被遗弃在世间荒原上的种子。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份救赎,芸芸众生纷纷逃遁到神邸中去。而历史也不乏宗教,不乏先知,不乏其神。然而荒诞的是,浮士德笃信上帝,却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皈依神明然后背叛,按照加缪的说法,这无异于哲学上的自杀。到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情况就变得更糟了:人类面临着被抛到世间的困境。人是他自身唯一的目的,这种无目的性决定了生命荒诞的本质。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死亡事件的必然到来更加剧了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理性的热望受到了打击,普遍的理性主义在人思维的非理性之处碰壁。于是,查拉图斯特拉说道:“偶然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并且试图以此绊倒理性
不过,我毕竟不是哲学家,我感兴趣的并非荒诞之发现,而是其后果。换一种说法,我总是试图去了解荒诞是否操纵死亡,或是说是否在直通死亡的逻辑。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加缪予以了肯定。他不无痛心地说:“在我们的世界里任何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一次次的控告,一次次的审判中,生命无声沸腾。偏偏庸禄之人热衷于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拼命抢占道德高地指手划脚,口诛笔伐,又有多少人千万百计地给对方设局,然后自己做局长。一切进行得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殊不知在其它局处人的眼中,这不过是为表演其荒诞行为举行的集体会演而已。
就像苏格拉底在临终辩词中所讲道的:“让我们分道扬镳,生与死,哪条路更好,只有上帝知道。”默尔索有着相同的豁达:“我期望在处决之日,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苏格拉底被判极刑,利默尔索被送上断头台,两千多年过去了,世界还是一点儿不变。以至到了今天,依旧是网络暴力,三人成虎。键盘侠管窥蠡测,一傅众咻。自2001年南京彭宇案以来,见义勇为者也要在无懈可击的社会逻辑下承担责任。傲慢与偏见同在,谎言与做作共存,生命可以多盲目,伤害就可以多彻底。若要以道德绑架人格,就把所有的人化作了真理的猎物。而只有“控诉”的手指并不指向他人,而是我们自身之时,我们才有可能从局外人那里取一份道德的意义。矫正国民心理之关键在于摈弃成见,保证法理公正的诀窍在乎抛却私见。否则,终有一日我们都将暴晒在骄阳之下,那些死去的意识和焚毁的信念会是我们焦虑的声音
关山难越,谁悲穷途末路者;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局外人。横批:满纸荒唐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