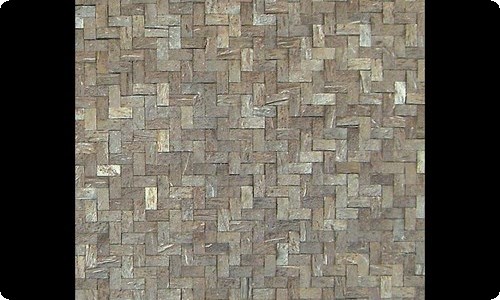两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庄子在闲静的午后静卧,他微闭的双眸和上翘的嘴角,正展示着他欢悦的梦境。恍惚间他身后长出一对翅膀,庄周化作栩栩蝴蝶飞舞在天地之间。然而豁然梦醒,庄子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发现自己是睡在床上的庄周,但那只在梦魇里飞翔的蝴蝶却再也挥之不去。于是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我是庄周?还是蝴蝶?
他住在穷乡陋巷,斜阳草树之中,享乐天年,布衣芒鞋,鼓盆而歌。倘若用笔勾勒庄子,应当用近乎白描的悠闲飘渺的线条画他的衣纹,用灵动疏放的墨色写他的鬓发,他厌恶乱耳的五音,迷目的五色而钟情于自然的高山流水风吟虫唧。他啸傲山林,怜花惜草,他淡泊名利,息交以绝游,知道人世间的尔虞我诈,不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知道繁华落尽必为凋零,故自然而生,自然而死,无欲无求。他的精神高高地飞翔在污浊不堪的泥沼之上,那是何等博大而辉煌的垂天之翅,他驱散着人类贪欲,残暴和自大的阴霾。庄子的思想是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那些闪着智慧之光的文字,悠然而至,带来林林总总自然的生命与言说,欢焉而去,留下了深邃广博的宇宙苍穹,以及,美和自由的人生。
美是什么?美在哪里?难道是世俗彩绘的国栋雕梁?是精致的陶瓷或墓葬的装饰?是五弦妙手弹奏的音乐?去吧,去吧,这都不是。这些矫伪的艺术,在庄子看来都是恶俗的,不堪的,不可容忍的,真正的美存在于天地之间,是没有经过人工雕凿,天然淳朴的存在。显然,庄子追求的是一种没有经过人破坏的天地醇和之美,一种纯真不加矫饰的自然之美。而一切人为之美的艺术,不过是一些摧残事物本性矫伪之作,这些东西与人为天性相执拗,必除之而后快。“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的美,是彻底的真和朴,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朋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你看那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水上清风,那浩浩江流,巍巍高山,层层林海。那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寒光积雪,苍茫的宇宙之间,何处不是无言的大美?
自然之美,正是美在率真和纯朴,毫无雕饰,灵动清晰,刻意雕琢可能美丽,但已失之于生动。人也应该如此。《庄子》中关于东施效颦的寓言,最能代表他的观点。西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都惹人迷醉。即便略施淡妆,衣饰朴素,也无法遮掩她的天生丽质。有个长得很丑的人叫东施,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时模仿西施的一举一动。西施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她的病又犯了,只见她手捂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这个样子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手捂胸口,双眉皱起从乡间走过,可是村里人看到她这样子,都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的走开了。这丑女人只知道人家皱得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丽质天成,哪怕陷于疾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动人心弦。那丑女人本已很丑,再以愁苦的样子,可谓丑上加丑了。
这个故事流传至今,人们以为庄子借此嘲笑东施的丑陋和不自量力。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不是嘲笑东施的面貌形体,事实上他也并不在意人的外在形体,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丑得奇形怪状但心灵淡泊飘逸的人,庄子都是大加赞美的,他在意的是你是否是个自然的真人,一个诚实本色、率性、纯洁的人,一个卸掉众多虚伪面具的人。
我们都经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就不闹,没有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恶坏人,全出自内心的情感而非虚饰和矫情,面对五彩的的世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只因好奇而非功名利禄之心。所有一切,皆自本性,快乐与悲伤、喜爱与厌恶毫无半点虚假。可是,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却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虚伪。痛苦的时候不敢放声大哭,拼命地挤着笑脸面对世人,开心的时候不敢开怀大笑,偏偏板起脸像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一面真实的感受生活给予的苦难和幸福,一面虚伪地掩盖面容上的喜怒哀乐,慢慢地,我们学会硬起心肠,不动声色。我们失落了自己的本真,同时也失去了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切最美好的都是最真挚的,只有能保持自己自然天性的人,才是精神的伟人,也才是永远快乐的人。相对于宇宙来说,人生何其短暂,为什么要逼自己背负各种各样的理想,使自己的心被奴役?假如世外有一双慧眼俯视红尘之间的财貌名利之争。看见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绞尽脑汁,刻意苛求,不再保持率真与纯朴,那它该如何悲悯人的愚昧啊!世事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全然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声音,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这样才能是一个合乎自然之道的人,才能是一个“美”的人。
看见拈花微笑的佛祖和迦叶了吗?见到鼓盆而歌的庄子吗?见到发现了“一切美的相同性”的苏格拉底吗?背离了自然的本性,才是让人越来越不快乐的根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