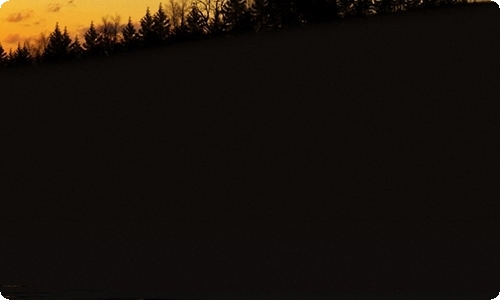
篇一:掬水月在手
G1811王子涵
如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一样,中国近现代语言的历史也是动荡的:世纪初一阵峻烈的西风伴随着文化的革新破除了古代语言的陈腐,但也同时摧折了那一片水草温润的古典诗意。当语言走入新一个千年,互联网的出现又以其浮浅直接震动和改变着我们原有的语言,正如毕飞宇所感叹的,“只有极限修辞才能构成日常的表达”。这种震动从语言一直传播到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上,使其流动不定,使它们之间高墙四起。
有太多的编造,极端和简化,我们听不清自己的话。正如有太多的观念和思想,我们看不清楚自己;有太多的变迁和摧折,我们看不清楚过去。于是,在今天,我们需要捧起诗歌这汪清澈的潇湘水,以求在手心里再次看到悬挂在天边的那一轮明月的光华,并以光华照亮自己,以明月充实自己。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正如海子所说,诗歌这一汪潇湘水反射出的是语言的光华。仔细想想,有多少语言的运用源出于从前的诗歌?如《诗经》中“桃之夭夭”到“前不见古人”,又如咏叹明月的诗句熔铸成我们对于相思和永恒的记忆。它们是一个时代最美的语言的集合,是一个时代语言建构的代表,背后凝结着丰富的人生体验、时代感受和哲学思考。
因此,读诗让我们在这个语言动荡断裂的时代恢复对语言的把握,在这个表意求快求浅的时代充实自己的情感。“不学诗,无以言”,孔子的话点出了诗歌对语言的充实作用。异曲同工地,有人解释我们为何要读诗时说了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你读了诗歌,面对湖上落日就能吟咏‘落霞与孤鹜齐飞’,临一轮落日,叹赏晚照;而不是‘我去!真漂亮!’,然后拍下照片走开”。正如此,诗句以其丰富充实了我们的表达,使我们能够发出心声而不受阻碍,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体验保有一份感知力。
进一步地,通过手中语言的月光我们不仅能照亮自身,还得以顺着月光看到那一轮明月,藉由诗歌触及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生命体验,越过过去和现在的断层实现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以古典诗歌为例。叶嘉莹先生,四处奔走讲授诗歌,要“把不懂诗的人接到诗里来”,其意不仅在传播诗歌之美。“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更意在帮助人们在这个传统文化渐渐走向“郢中白雪无人和”的时代体认我们过去的情感和思索。通过诗歌,我们抵达过去,而只有看到过去,才能更好地向前。
再进一步,通过体认那轮明月,我们修养自身,让历史的月光充实我们年轻的心。就如叶嘉莹先生一生经历战乱流离,却始终保有一片“温柔敦厚”的君子心性。她的一位朋友感叹“正是诗歌救了她”。正是背后古代诗人的精魂——他们的生命体验,他们的人格养成了这样一片君子心性,亦即正是古典诗歌让我们把“君子”的明月捧在手中。黄永玉先生感叹沈从文先生像水一样既坚韧又柔软,这和他成长中的诗情——正如在《边城》中表现出来的一样——亦有关系,也正是他故乡清浅的诗与歌,让他把同样清明的月捧在手中。
“太初有言”,正如此,通过语言我们看见自己,看见历史,看见哲思。而诗歌是语言的明珠。于是,当当代的奔突躁动的风吹袭我们时,不妨俯下身子掬起一汪诗歌的潇湘水,而再一次在手中看到那一轮明月,在心中贮满月光。
篇二:诗与人生
G1811高雨菲
诗是语言最精炼,表意最具感染力的一种文学形式。《毛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揭示语言是将内在情感思想外化的工具。诗歌也因其独特的形式,更准确、动人地传达着这种情感。从而,诗离不开人,人亦离不开诗,诗与人生密不可分。
诗歌承载着人生,失去了生命感发的诗不可被称作好诗。诗词固然有其形式上的要求,但并非只要符合字数一致、对仗工整、韵脚和谐的都是好诗。不久前,人工智能作诗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输入几个字,不到几秒内就能呈现一首像模像样的诗来,足够唬人。但细细读来,虽然词句间内容相关,但逻辑不通,也没有动人的情感。究其原因,则是文字背后缺少人生的起落,生命的感发,“为赋新词强说愁”。叶嘉莹先生在她的唐宋词讲座中说“诗的好坏不在你是用典故或是浅俗,而在于你是不是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和感发的生命。”质实如李后主,“林花谢了春红”也打动了无数易感的心。诗词的舞台上有太多种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不论是清新还是沉郁,豪放还是婉约,都应看重一颗生命感发的心。雄心壮志、一往无前的政治理想与不被重视的现实处境在诗仙心中激荡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宣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忘我与现实中老、病、独、衰的艰辛在诗圣心中纠结成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感叹。生命的矛盾与张力成就了诗的精彩,感动着一代代读者。
反过来,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需要诗,没了诗的人生失去了一抹光彩。文学大师王鼎钧说过“如果没有诗,吻只是触碰,画只是颜料,酒只是有毒的水。”诗可以说是为我们内心的悸动找到了一个归宿。古往今来所有亡国去乡者,都在《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中看到了自己;多少感时伤逝者都目睹着最后一篇秋叶飘落,在《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中找到了共鸣。带着心与心的共通,我们得以越过生命中的苦难。与其问为什么在经历了青年丧母、去国离乡、中年丧女后叶先生仍坚贞地踏上弘扬传统诗词的道路,不如说是诗的感发渡了她一劫又一劫的悲痛。“只要雪有影、雨有痕、雷有声、水有纹,就有诗”,而我们也因那“一阵惘然”,就要读诗。
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什么一定是诗?白话的普及无形中拉远了我们与古典诗词的距离。同时,不论是古典还是现代,诗歌以象达意的基本表达方式也成了理解上的障碍。许多因素出于人们把“诗”和“远方”划上等号后的敬而远之。实际上,散文或其他文学形式与诗相比,缺少的正是那“低回往复,缠绵不尽”的情感表达。而对于我们情感中国的复杂、隐秘、幽邃,最好的抒写方式与阅读方式就是诗。一句“人生长恨水长东”,道出愁恨的强、深、久、浓,但再多的形容词都不足以说清“水长东”三个字给人的感动。这也即是诗的力量。所以,诗的价值值得我们跨越语言与理解障碍,去体味,去发现新的世界。
诗离不开人生,人生也离不开诗。从数千年前周统治者采集百姓心声,用诗歌、礼乐教化是开始,诗便是一种自然的,由内而发的语言。不知不觉,传唱至今,刻在了我们的基因中。所以更多时候,无意识地在人生的经历中吟上一句,我们不觉回想赞叹,那真是一句好诗。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与人生融为一体,诗即人生。
篇三:诗的长夏
G1813闾斯容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观影后久久不能弥散的震撼,一部分来自叶先生站上讲台的风华,追忆往昔的从容,而更大一部分则源于影片中余韵悠长的诗——带给苦难人生如此多的救赎,给予眼前生活一个浩荡的远方。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寻觅自我、笃定自我、回归自我。
诗歌异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最大特征,即是用意象堆砌出环环意境,引人入胜又难觅其踪。人类在数千年的进化中,已不善于运用简单而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一腔离愁凝噎在心头,难以言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面对永恒时的渺小彷徨,无以言表。浓烈和深沉涌起时,复杂的心绪唯借诗歌方能聊表一二。踏上创作诗歌的路途,人才有机会剖白内心,找寻纷繁错综的意象下,刻意雕琢出的真挚与珍视。
每一首诗的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都是独特的,它见证着一个个生命沓来时的行迹,同样也赋予它们随心远去的权利。“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的诗人,某时某刻也正经历着“蓦然回首”那一瞬间;人们慨叹于“应似飞鸿踏雪泥”的恣逸,但同样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哀婉表示理解。十四行诗允诺莎翁安放他的爱情,散文诗则给予泰戈尔的想象以栖身之所。没有谁会拿刻板而教条的准则评判诗的优劣高下,正如人生来并无尊卑贵贱之别。人性的多元于此得以被包容,自身的价值于此得以被肯定。诗歌予迥异生命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和自由,人们徜徉诗海,绽放光华,悦纳生命,笃定自我。
诗模糊了时间的界限,消磨了空间的隔阂。如今我们仍能听到那声无奈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同为周室衰微喟然叹息;我们也曾与拜伦一起设想过:“他日相逢,事隔经年。将以何贺你?”大音希声是人类的共鸣,因此,只好回应“以眼泪,以沉默”。诗人将诗歌的起点安插在不同的位置,履行生命时,也走在不同的路上。但相互瞭望的星星,一定会有交汇的轨迹。每首诗诞生的背后总承载着一群人过往的思考,一段留有余温的历史。立在时空尽头回望,不惧将来,不念过往,因为我们总能在诗篇中回到最终的归宿。
但需谨记,诗于人,决不是一件附庸风雅的高价商品。吟咏吐纳,含英咀华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追求“腹有诗书”的境界。当人们刻意强调诗词大会总冠军雷海为“外卖小哥”的身份,当人们乐意将关注点放在才女武亦姝考上哪所大学时,一切将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诗歌的光芒将会轻易地被功利这抔土所掩埋。这颗遗失在夜海中的星,原应点亮一片诗意的世界,让人们在对诗的品味、体悟、创作中感受到人生的融入,洗净人生的铅华。
好在诗的长夏永远不会凋歇,愿你我在不朽的诗篇里与时同长。
篇四:诗与生命
G1813 高茗浩
庄子有云:“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望着天边的云朵慢慢翻卷,手中的时间缓缓流淌,生命总是困囿于岁月与年华的流逝,不可避免要在有限的时间中选择自己最欣赏的面貌。人们不禁在此时轻轻对自己发问:“我的生命,究竟应该是何种模样?”
依我看,生命,应当是有诗意的。
一个人的生命不能与自己的灵魂脱离而存在,余光中有诗这样说道:“握你灵魂的尖端,纤纤有五瓣”,而我相信其中必然有一瓣,是独属于是诗的。这是因为,灵魂本来空虚,需要我们用一些东西来填满,人们将这些东西分作两类——理智与情感。诗歌,则正好可以成为二者共同的寓寄。
理智,是人对于自我的认知。它像一面镜子,映着脸庞,又映着心灵的光。纳兰一句“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是对自己存在之所识,在这世间,他平凡却又独特地绽放着;于谦一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对自己所守之道之所识,纵然千百般锤炼,清白坚硬之本性从未改变;杜甫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对于自己向往之所识,不求自身锦衣玉食,但求为天下人谋一丝温暖。生命该是何种模样?他们在诗中进行了回答。
情感,是人对于世界的反馈。每个人心中,何尝不是都有万般情感不断流转,而诗歌便是乘着情感的一条小船。这条船上,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亦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直爽,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激烈,亦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忧伤。如果说生命是条长河,那么这条小船,必然会始终随波浪向着前方。
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诗,不是因为他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别样的光辉,而是因为每个人的灵魂,本身就为诗留下了一隅。一个人如今的气质里,不仅藏着他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更藏着他写过的文字,吟诵过的诗篇。若生命中少了诗,灵魂则会变得脆弱无依,或许一阵风过便靡有孑遗。
当然,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有诗意,并不是奢求每个人都能如曹植七步成诗,身负惊世之诗才,更不是要求每个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能作诗也能吟”,掌握多少必背古诗词。诗歌之于生命,固然是一份美好。不过亦有许多人,我们从他们的生命中,读不到如诗歌般的考究与细腻,但依然可以感觉到那股优雅而绵长的诗意。
王小波以其语言的简洁与朴素闻名,但当我们念起“今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吃,想爱,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其中诗意是不言而喻的。在他不多加粉饰的外貌下,生命却自然而然流露着诗意。与一生中遇到大大小小的规矩与要求不同,诗意不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硬性指标,正相反,它是一种对待生命的独特情怀,随性而自然。
人时常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生来似乎都在寻找,寻找自己前进的方向,寻找生命的归宿所在。疲了,累了,便在大路上席地睡着;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又或者张开双臂,躺在随便一块草地仰望。
生命是简单的,简单地来临,简单地度过,简单地离去。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却又都相同。然而生命又是美好的。睡醒了睁开眼,发现到下一个村庄的距离已经不长;坐在石头上;看着对面丰收时节的田野上,翻卷着金黄;夜色下的天穹,有永恒的星河在陪伴着行路人的仰望。这就是诗意,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行路的终点,而就在行走的路上,诗意让人们不踯躅于眼前的苟且,而是一路哼着小调,一路风光,走啊走……却已然足够了。
灵魂对诗意与生俱来的渴求,以及人对于生命形态后天的追求,二者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意对于生命的不可或缺。人这一生,定当有诗相伴而行。
所以,请给生命以诗意,给明日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