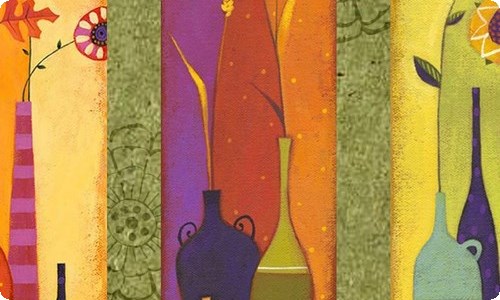
我无意中翻到过姥爷少年时的照片。
那是在牧区,姥爷留着遮住眼角眉梢的刘海,怀中抱着只小羊羔,倚在围栏上肆意快活地笑。即使是略略泛黄的黑白底片,也难掩盎然的意气风发。那是姥爷的十六岁,他已经准备好了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幼儿园时我同姥爷最亲近,总是紧紧攥着他的手,同他走过夏蝉冬雪,春华秋实。我们走过房前大片大片的花园,他会停下来教我辨别花与叶的品种,毫不在意我会不会迟到,为此我总是收获老师漫长的喋喋不休。在我眼里,姥爷是非同一般的艺术家。他会在带我和表哥去郊外捞鱼,养进盛满水的浴缸里,我们总会湿淋淋地被姥姥罚站在院外。那时,他就一手牵着一个,给我们唱他自己编的歌。也会因为跑调太丢人而把锅甩在表哥身上。温和晴朗的天气就去下象棋,遇到阴雨连绵就同姥姥编花绳。兴致来了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带我们寻找外星人的痕迹,在我们觉得快要发现真相时告诉我们都是假的,再得意洋洋地留给我们遍地狼藉。
他是个极具生活情趣的老小孩。
家里人总喜欢在聚会时揭开过去的帷幕,让我们这些小辈从中窥得一点他们年轻的剪影。我们剪切拼接,终于得到了他人口中的姥爷的过去。
我们总在想那样渊博有趣的人,定是以精力、时间与爱滋养大的。但那时对厚重的历史模糊不清的我们,不知道那些对于一个尚且天真的孩子意味着什么。那些混淆是非和流言蜚语把他独自逼到了茫茫草原,却意外成为那里的恩底弥翁。过去的伤疤被他细细掩盖,用时间与工作分散疼痛对他的影响。家人总对那些苦楚讳莫如深,我们只能在他们醉酒时才能听到含泪的只言片语。姥爷在那时是平淡的,是没有颜色的。
时间与天赋成就了他,苦楚与灾难没能打倒他。姥爷活出了我梦想中的样子,英雄白头却保留着一颗稚子心,历经苦痛仍坦然处之。
愿时光对他仁慈,让这位老人仍怀一腔年少,陪我们走过漫长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