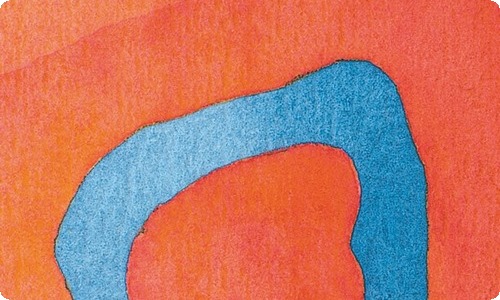我的外公是一个工程师,他这一辈子生命的热情几乎都献给了建筑。
外公又高又瘦,他的脸上布满了如波浪般细密的皱纹。当他眯着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的时候,那些波浪就聚在一起,当目光再定格时,那波纹就像两朵小菊花一样,密密地盛开在外公的眼角。
儿时的我每看到这两朵小菊花时就会呵呵笑上几声,可是每当笑声一大,外婆就会赶忙跑到我身边,轻声又温柔地对我说:“小声点,你的外公在研究图纸。”
不懂事的我经常对外婆做鬼脸,然后我就会爬到外公的椅子旁,看着他在一张蓝色的布满直线的图纸上画着什么,他的左手则捏住图纸的左下角,随时准备翻下一页。看着看着,我就在椅子边睡着了。
童年时,外公就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灯光下认真写字工作的背影。
现在外公经常出差,临行前的一晚会带一小包换洗的衣服,带一大包他工作用的东西。他离开时,总会用他那满是厚茧的手朝我挥一挥,然后便大声地对我说:“锐锐再见,想我的时候可以和我视频通话哦。”这时,我也会点点头,对外公说再见。
外公如果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带我去散步。每次散步都会去有高楼的地方,走到高楼前,外公都会停一停,抬头仰望它们,那些建筑的影子就会印在外公那澄澈的瞳孔上,在他的眼中那些建筑总是那么明亮。微风拂过他那古铜色的脸颊时,我总会看到他那淡淡的笑容,这笑容中藏着外公对这些建筑的赞许。
在回家的路上,外公总会兴奋地与我谈论这些建筑,他就像一个孩子找到一些新奇的小东西一样。有些专用名词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我知道,谈论这些建筑是外公唯一的爱好,而身边小小的我,不过是他虚拟的知音罢了。
走在回家的楼梯上时,外公的皮鞋跟敲击着台阶发出“咚咚”的响声。外公平时只穿皮鞋,而且每次出门时都要把皮鞋擦得闪闪的,他的黑裤子和白衬衫也受到他格外的珍视,每次回家都要用毛巾拂一拂,掸一掸。
而掸完灰的下一秒,就是回到他那经常坐的椅子上,再次搬来他的图纸,将老花镜轻架在鼻梁上,右手拿笔,左手捏纸,又开始与他的图纸打交道了。
这半世风雨,外公用他那隆起血管的手勾画出了多少建筑?那层层叠叠的图纸,在这岁月中换取了他的多少笑容?童年时代,外公端坐在桌前的背影,他的皱纹,他的白发,他敬业、认真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优选]四年级写景作文](https://img.puzw.com/upload/11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