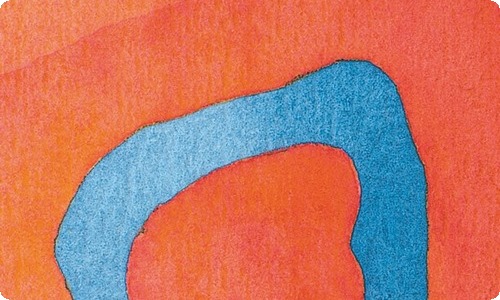她竟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连我手中那张白纸都变得了无生息,她还在笑,那口白牙比那张白纸还要亮几分。
她把眼睛瞪得老大,嘴唇扯的越来越开,那白牙在日光灯下,仿佛刚长出来,开始泛光,她笑得越来越大,世界都被她笑进去,还有那盏灯,那白牙在日光灯下仿佛刚长出来,比那张白纸还要亮几分。
白纸变暗了,还有那盏照亮她白牙的日光灯,没人叫过她的名字,其实她一字一笔都记得,她的嘴巴扯的越来越大,她那样清楚地看到无声的血液流过"淑"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撩。她的眼睛瞪得老大,她还在笑,世界都被她笑进去。
红瓦白砖,瓦白砖红,她的人生总不过一声婴啼开始,一瓦瓦堆砌起来梁横柱直的房屋,她叫得急促,房屋被一阵用力的婴啼包围,她喊的那样紧张,那样急切,她的人生总不过一场婴啼开始。
几年前的生命被一阵风吹起,一丝重量也没有落下,天明明黑的很,她却张着一口白牙,眼睛瞪得老大,月光就照在她的白牙,她的眼睛瞪着月光,于是几年前的人生变得支离破碎,她的嘴裂的越来越大,世界都被她笑进去,她为她的生命带有"淑"字而笑,她为她对面手舞足蹈的人而笑,淑雅端庄,大多数人都一声不吭,每一张脸都被她的眼睛泛过去,那白牙在日光灯下仿佛刚长出来。

![[优选]四年级写景作文](https://img.puzw.com/upload/11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