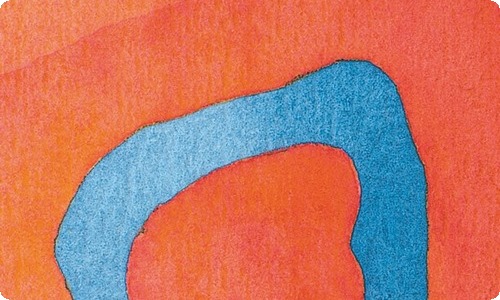外婆买了一打小鸭子,圈在围栏里。栏里一个大水盆,早被嬉戏的鸭子们搅成了浑泥汁。鸭雏扑腾着水花,又追逐着滚到土堆里,一绺一拉沾满了土粒子。外婆却不理,仍旧圈起来,丢些烂面片,任其折腾。
外婆插秧去,叮嘱我在家看鸭子。五月的骄阳热力四射,那只讨厌的黑猫也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就不安生起来:找到一根隔年的芦杆,头端系了一个红色塑料袋,稍微有些三角形样子。圈门一开,小鸭子撒欢涌出,摇摇摆摆,无师自通的奔向宅前堰下丁河去了。
说也奇怪,这些头重脚轻、走路不稳的鸭仔们跌跌撞撞地奔向河里,一得了水,犹如游龙得了雨雾。三三两两,欢快地沿河向东游去。我志得意满地瞧着自己的杰作:鸭雏们沐浴以后别提有多鲜活,多精神了。那灰绒绒的背,那亮亮的紫色嘴壳,那欢愉的烂漫,浮在清碧的河水上,像一首欢乐的诗,一阙无词的曲,一汪恣意的天籁。
我学着牧鸭人的样子,抖动着芦杆。可是,小鸭子却仿佛受了催促,游得越发快了。我在岸上,鸭子在河里。这些精灵可比我自由多了,它们游泳、嬉戏、寻食,看蓝天白云,听水流鸟鸣。我拨拉着绊腿的芦蒲,深一脚,浅一脚跟随着。小鸭们却不领情,越发奋力游得更快了。也许水草扯了脚,也许游速太快,重心不稳,有一只鸭雏突然侧翻了,它拼命挣扎,在水面上打转。我急得头上冒了汗,连忙用芦杆稍拨转,它却挣扎的越发厉害,忽然就不动了,远远地软瘫在河面上。其余的鸭雏也慌了,一齐弃了它,四散游去。我盯着那只软绸一样的小生灵,心中满是悲伤。
鸭群继续往前游,我越发小心了。可是稍不留意,又有几只接二连三地死掉。也许我太急躁了,我不该“赶”鸭子。我放慢了脚步,回头看了看,远远的村庄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影了。小鸭们也放慢了速度,慢慢寻食。河水缓缓地流,青碧青碧的。鸭雏们沿着近岸的水草边缘前行。河水突然有了异样,一团黑黑的涌动的活物在河面下缓缓移动,靠近了鸭群。鸭群突然骚动起来,钻上钻下,左摇右摆,每只都忙不迭的吞食。原来,鸭群撞上了一群小乌鱼,好一顿饕餮盛宴。水面瞬间打个大旋,一只小鸭子就消失在漩涡里,其余的鸭雏们一哄而散,小鸭子被潜伏水底的大乌鱼吞了!
水面又恢复了平静,我的小鸭子只剩下五只。我再也没有心思牧鸭了。看着它们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机械跟随。午后的阳光热辣辣的,我又渴又饿又累,环顾四周:农人在田野里割麦插秧,布谷鸟在天上起劲得叫。恰好碰上一株野桑树。紫红的桑葚果挂满枝头,我压弯了枝条,大块朵颐。
堰背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
天上白云轻悠悠,
水里鸭儿慢慢游,
枝上柳絮吹又少,
思乡人儿梦里头。
丁河水儿清又亮,
丁河鱼米稻花香,
村南哥哥去插秧,
村北妹妹来采桑。
歌声渐转苍凉悠长,我也沉醉其中,忽而就醒了。咦?小鸭子呢?河面上漂
来一截捕鱼的丝网,上面挂着五只软软的鸭雏,被缠得死死的。
我终于明白外婆为什么不放小鸭子下河了。暮霭四合,丁河岸边,踟蹰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她的眼前似乎还晃动着十二只鲜活的小鸭子的身影……

![[优选]四年级写景作文](https://img.puzw.com/upload/11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