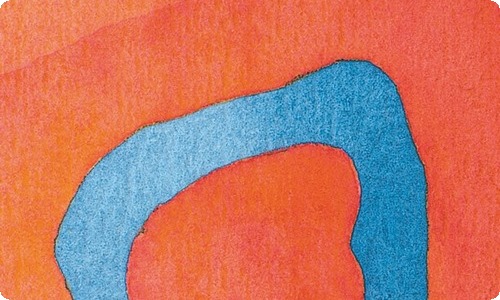美妙又梦幻的童年里,最理想的玩乐场所就是我家的诊所了。
每次看见宝宝打针那“威风”的样子,像一位战士,我既羡慕又渴望,脑海中不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我穿着白如雪的白大褂,戴着乳白色的口罩和手套,眼睛前还配着一幅眼镜,带着一丝博学气质!慢条斯理地给人打针……
每天晚上关门后,我都会兴奋地穿上爸爸那大大的雪白的大褂,戴上哥哥的眼镜,又套上自己的白手套,戴上口罩,武装完毕后,便开始了一个人的游戏。我从抽屉里取出针头与针管,里面装满白开水,先用那尖锐又令人害怕的针头到处喷射,好像电视里打水枪一样,有时瞄准一个点,快速地射出一颗“子弹”,正中靶心,有时躲在一个角落,用犀利又敏锐的目光扫过前方又黑又神秘的地方,时不时迅速把目光闪到一个点上,紧盯着,一会儿又侧耳倾听,一听有什么声音,立马把针管架在桌子上,谨慎地装模作样地向一个角落射出“子弹”。有时翻个跟头,闪到一个地方,假装躲过敌人的攻击,从嘴里发出“砰砰啪啪”的枪声,随之射出“子弹”。
玩过了像战士一样的医生,我又扮起专业又严肃的医生来。
一开始,我就板起脸,皱着眉头翘着嘴,一脸冷酷与生气。我拿来一块海绵,当作人的皮肤,我瞪着那海绵的红点,小心翼翼地拿起针头,缓缓向红点移去,针刺进去了,我演得越来越紧张,头上冒出一滴又一滴冷汗,我咬紧了牙关,把细细的针头刺进去。“好了!”我高兴地喊,只见针头已在红点上留下一个洞,红点被针管里的水冲洗掉了,我松了口气,拍着胸膛,庆幸自己没失败。
我玩完了打针,又开始了听心跳。
我拿起听诊器,带上。把听筒慢慢放在自己胸口,只听“扑通——扑通……”的声音逐渐消失,我皱了皱眉头,懊恼地抓了抓头皮,继续听。我往左移,那声音越来越响了,“快了!快了!”我兴奋地自言自语。“好了!一切正常”我大喊,心里十分开心。
这一次次的游戏依旧不使我厌烦,因为这一次次的游戏给了我无尽的快乐。

![[优选]四年级写景作文](https://img.puzw.com/upload/11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