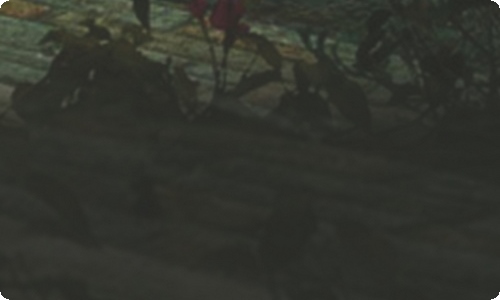
小时候,每当我昂首问姨父何物最美丽时,姨父总会用温暖的大手轻抚我的头,微笑着不言语。
我小时候时常去青岛的姨妈家串门,那时与我玩得最“铁”也最疼我的就数姨父了。那年夏季,归期将至,姨父深知我对姨妈家后院开满的栀子花精有独钟,便提议我去摘一朵开得最美丽,最大的花夹于一本书中,做成标本,待来年姨父到我家时带来。就这样,我们将我们之间的约定藏于一本红皮书中,望着书页中的那抹纯白,我笑了。
但是,日夏一日,年夏一年,姨父始终没有来,这个约定也迟迟未被兑现。我又气又失望,开始拒接姨父的“长途问候”,恰恰又因家中诸多不便,之后我便再未去姨妈家。
就这样,时间河流冲走了许多,冲走了我的稚气,也冲走了我记忆中的“红皮书”。
不曾想,时隔多年,再一次来到姨妈家,映入眼帘的却是黑白丧服,传入耳中的是阵阵痛苦声。我不愿相信这一切,直至灵堂,大脑一片空白。我楞楞地立在那里,眼神空洞地望着灵柩。不知是谁递于一本书,似曾相似的红色。我急切地翻开已微微紫黄的纸张,不再纯白的栀子花标本赫然显现在我眼前。我轻抚其旁用苍劲有力的字体书写的祝福语,心痛如绞,将书抱着怀中,痛苦失声。原来,我们谁都没有负约。
相离莫相忘,天涯若比领。我懂得姨父一直在履行着他的约定,同那洁白的栀子花与祝语般一直守护在我身边。
约定,真是美丽。




